胶东半岛
过年蒸“饽饽”
胶东小镇的家庭主妇们,过了腊月二十就仿佛琵琶曲直接奏到了高潮,大弦嘈嘈如急雨,攒了一冬天的力气在这八九天大显身手。最能体现过年仪式感的,就是花样繁多的面食。
这时候,平日的主食馒头是被人嫌弃的,因为它做起来太简单,长相太普通。主妇们喜欢做的是饽饽,枣饽饽寓意早交好运,桃饽饽让坏运气赶快逃走,岁饽饽祈愿家里小孩心眼明亮……一言以蔽之,过大年,蒸饽饽,期盼着来年日子蒸蒸日上,红红火火。
饽饽是一种做工复杂的面食,做好它是对主妇体力的一场大考验。主妇们都有一个大面盆,倒入半盆面,和面,面团发好后放在面板上反复揉,用胶东话叫“守面”。这是最难的环节,不仅考验胳膊的力气,还需要后背和腰的配合发力。母亲通常跪坐在炕上,上身前倾,这样有利于发力,不停地揉、摔,面守得好,蒸出的饽饽才劲道、纹理细腻。这个过程我通常帮不上忙,母亲常边做边数落自己的懒丫头,一点都不学,将来自己过日子怎么办。家乡的人认为面食在各种食物之中居最重要的位置,即使我现在炒得一手好菜,母亲依然认为我不太会做饭,可不是么,一个只会炒菜不会做馒头包饺子的人也好意思夸赞自己的厨艺?
面和好后,就到了主妇们施展才艺的时候了,手巧的把面揉成“聚宝盆”“石榴花开”“鱼跃龙门”等等,那简直就是一件件工艺品。母亲手不巧,我们家就做最简单的桃子、神虫、枣饽饽等。小时候我最喜欢守在面板旁边,看着母亲小心地在造好型的饽饽上挑起几个孔,我帮她把切成细条的枣插在孔里,顺便往自己嘴里塞几个吃,甜甜的金丝枣,吃起来比糖都美。
蒸出一锅香气馋人的大饽饽,要用胶东特有的灶台和大锅。柴火在炉膛里噼里啪啦地响,锅里的水汽溢出来,弥漫了整个灶间,饽饽的香气充盈其中。出锅后的饽饽,还要盖上红彤彤的印记,饽饽们立马有了精气神,洋溢着过年的喜气。
除了饽饽,人们还要做大包子,不同于南方小包子的眉眼精致,它们的个头通常都跟壮汉的拳头一样大。主妇们忙活做饽饽、包子,一直能持续到年根,够全家人吃一正月。如今做得少了,通常也有十天半个月的量。做好的面食一般都放在大笸箩里。
前年我回家小住,母亲让我帮忙,把家里的旧笸箩拆了当柴烧,编笸箩的篾片,在炉膛里燃起来有呛人的味道。随着父亲离世,我留京工作,这几年过年母亲不是在北京,就是和妹妹两个人在老家,年前蒸一锅饽饽、一锅包子足矣,母亲也告别了别家主妇年前那样繁重的劳作。我们家的烟囱,基本上很少在半晌时候升起炊烟。
在我老家,面食中地位最高的要数饺子。饽饽、包子是正月里的日常吃食,饺子是正日子的明星。年三十晚上守岁,大年初一早晨迎春,初二晚上送年,正月十五闹元宵,饺子都需隆重登场。在北京的家里,我和爱人对饺子并无太多热爱,通常就年三十吃上几个,别的日子也就一如平常。母亲多次笑我们初一早晨还喝豆浆,“想着日子过得好,打头一天就不该喝稀的”。
细细想来,母亲的笑里充满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在她心里,家庭主妇就该忙忙碌碌,捶捶酸痛的腰,揉揉发胀的胳膊,热火朝天地劳作才是过年的景象。看着宝宝熟睡的脸庞,想着将来一天我郑重其事地说话,长大后的女儿一笑置之,置若罔闻的情景,我突然心里有些微微的酸意,我仿佛看到,我和母亲的形象重叠,并无二致。照顾第三代甚是辛苦,不过今年我决定烦请母亲辛苦下,大年初一早晨全家吃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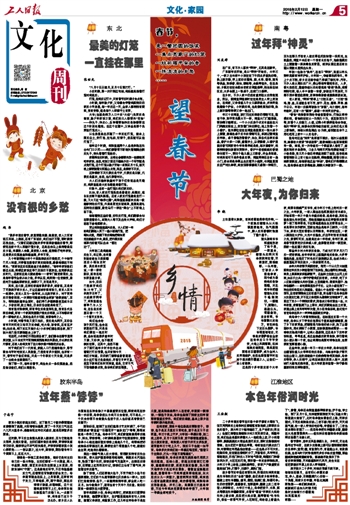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