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前农村“空心化”的观察不同,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为什么离开?为什么不荣归故里?
乡绅记忆,迷失在通往城市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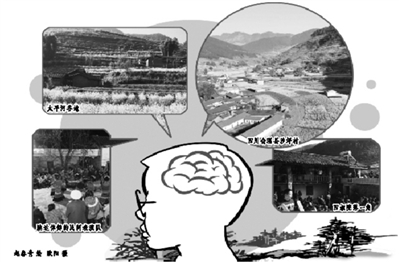
赵春青 绘 欧阳 摄
上一个春节期间,一篇关于“乡村未来迷茫”的博士返乡手记,搅动了众多内心弥漫乡土情结的文士。猴年前夕,网络上有人谈及乡绅的消失,谈及乡村的命运,失望、感触的论调又勾起更多人惆怅的情绪。
和以前农村“空心化”的观察不同,人们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挽留或是重构那个在离土离乡潮流中,依旧存留在记忆里的乡土画卷: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田园。
为什么离开?为什么不荣归故里?蔓草般杂糅的思绪中理不清答案。
时逢春节返归边陲故里看望老父娘亲,际遇乡绅后代70寿辰,我决定去看一看。
寻获:“乡土中国”旧迹
从西昌出发,行京昆高速公路,穿过安宁河平坦的谷地。在永郎镇下高速后,转蜿蜒翻岭越沟的108国道。经过3个多小时的行程,抵达县城会理。
会理旧时或许有些坚固的城墙已经难寻踪影,漫步街道,间或可以看到4A级风景区建设的横幅。“风景区”所依据者大约是狭窄、规整的老城街区,以及不少留存下来的临街木板墙、屋顶灰瓦的建筑。不过这些“古旧的遗迹”看起来有些残败,不像众多旅游发达地区那样整修得悦目有序。最遗憾的是街道十字交汇中心的鼓楼,虽然当地人告知是一直保留下来的,但怎么看都觉得是新建的古迹:完整光鲜的砖面和亮白的缝隙,使人完全找不到修旧如旧的现代文物理念。
也许正是迟缓的观念变迁,就如“老城”所展示的那样,会让我在这个位于横断山脉边缘的乡村,寻获一丝内地早已不存的“乡土中国”旧迹。
出会理向东偏北,继续行进,走上乡村公路。只能够两车错行的柏油路面平整地几乎完好,危险、急弯路段防护栏齐备,想来应该是新建成不久。沿途摩托车不断,微型箱式客货车频频闪现——透着富裕发展的乡村活力,我们只能慢速行进。3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这已经很不错了,据祖上土著于此的同行大哥刘华说,以前这段路坑洼不平,再有雨季泥泞、砂石障碍,多有耗时半天的时候。
这一路除了一个小镇子都是田野风光。南国春早,尽管才进入正月,地里的油菜花却已盛开,尤其是进入目的地太平村河谷,和传说中许多乡村小块地撂荒的描述不同,窄而不平坦的小河谷中,错落有致且细碎的地块完全被生机勃勃的作物覆盖,黄色的油菜花铺满太平河两岸,一片生机。
客观说,离城进山之后的行程,在良好的乡村公路之外,撇开马路边上不时出现的砖混建筑房舍,整体的感觉会让我回到30年前熟悉的乡野,路上的行车、人的衣着,以及居所虽然多有变化,但田野的乡村似乎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令人“迷茫”,如若产生诗情画意渐行渐远的感觉,恐怕也该是心理上的因素居多。
终于,目的地到了,走过摇晃不定的铁索桥,坐落在油菜花间的主人宅邸来到了面前。
窥视:“乡绅”的遗迹
促成这次探访之旅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乡间的景色,而是主人的声望。
昔日的沙坪村属于诺苏和汉人杂居的地区,不同族群之间汉族习惯、诺苏风俗交错。作为当地望族,诺苏血统的豪绅不仅精通汉语,族群也以汉姓刘氏知名当地官府和民间。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刘氏头领已然拥据沙坪河北岸方圆数里的田地和山头。有传说称,刘氏振臂一呼能够聚集近千人的队伍,而这应该是诺苏传统:诺苏不同家支(传说中同根的族群)之间械斗常有,威权和声望需要有武装来支撑。
少时学习刘文彩故事,曾问询过县里政协会的奴隶主,是否大地主都个个狠毒。想不到奴隶主们摇头,以经验答复说:除非是对外,狠毒者难长,欺压邻里无异于树敌,若遇家支械斗,难逃被自己人“谋害”,成功的头领勇猛之外还必须宽仁,似有爱兵如子的味道,善待族群,至少不逼迫本族壮丁,才会拥有一致对外的实力。
据已逝长辈昔年的回忆,刘氏即为良善地主,风调雨顺之年收租,天旱地涝岁月放粮,在当地很有名望。此外还有开明口碑加身:不仅送子到会理接受汉语教育,还邀请先生在本地开办私塾……所有这些,都让人想到内地的乡绅,既是秩序的维持者,又是文化的传播守护人。
各种传说都是很晚近发生的事,远远后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就时序延展推想,也许真能窥视到乡绅的遗迹。
待到新旧社会交替,末代头领聚众护院,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留下的几个少年,承袭了开明的家风,识文断字的长者毅然捐出了家族所有的财产,成为新队伍的一员。上世纪80年代,城里的老大挑头和兄弟在故土重建了宅院——被多次分配拆建的旧居已经不可复得,刘氏一脉重新获得村民的敬重,跻身“长老”位置。近些年长辈先后故去,只留下人称四叔的老四留守故园。
承继:“乡绅”的遗韵
将一地的鞭炮碎屑留在身后,进到院落,100多平方米的院坝坐满了吃流水席的,一轮又一轮,络绎不绝的恭贺人群从中午一直到傍晚。站在两层的正房前,听闻台阶上一位坐着的老者感叹:已经100多桌了!这样的情形要持续三天。
入夜,大红灯笼张挂起来,邻乡赶过来的达体舞表演队一身诺苏服装登场,唱歌、跳舞,喧闹声中寿星四叔一个人站在屋顶平台的角落,我上前叙话,一脸慈祥的四叔细声回复着我完全听不清楚的话语,后来才知道四叔耳朵已经不灵便。到深夜,一阵礼花焰火鸣放后,庆典的主题——生日祝贺也随孩子们分食六层蛋糕圆满告一段落。忙了一天迎送客人的小二(四叔的次子)送别表演者。表演者坚持不收取酬劳,在四叔的坚持下她们没有把持住。
也许是客气,也许是表达敬意。欢乐场景中我不时看到人们上前表达对四叔的敬意,而四叔当村委会主任的长子仿佛有些被冷落了,这大概就是“乡绅”的遗韵了,虽然乡绅没落了,乡土社会的威权逐步被政权系统的官吏等级取代,但乡长或者是村主任这些制度下的安排,并没有彻底替代文化伦理近乎自然传承繁育的乡绅选择。
而作为曾经的“长老”继承人,四叔及其村主任儿子也没有被资本欲望扭曲。村子里烟叶的种植和复烤,培育出不少富裕的家庭,那些沿河新建的钢筋水泥新居,与夯土墙的村主任“大”官邸相比,已经拉开了不小差距,这是同内地很多地方不一样的风景:乡绅的自律还在延续。
抉择:“乡绅”的未来
不过这并不是全部,农耕的乡村社会正失去世代相传的族脉凝聚力,那些传承人的光环:文化领袖和灵魂,渐渐没有人去承继。四叔的另外两个儿子离乡多年,在城市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正在省城读书的村主任儿子也表达了绝不回村子的意愿,喜欢街舞的他不只是看起来是城里人,也完全没有种植烤烟或者是农作物的技艺。
回过头来看1000余人的沙坪村,即便没有城乡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巨大差异,也不可能在文化、物质领域同城市等量齐观,人们在面临自己最后归宿的选择时,留居医疗保障良好的城市安享晚年,才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天早晨,我吸吮着清新的空气走在水清如泉的沙坪河边,看到沿河满处散落的现代塑料垃圾,意念中充满诗意温情的祥和乡村还在吗?乡村本身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对乡村未来的迷茫,难道就不是主观的臆想吗?迷茫的是离开的人,乡村自己并不迷茫。
吃过早饭,携同村主任的两个儿子走上了回城的路,此时我才意识到,乡村的路不是为了进入,而是方便离开,路和网络带进乡村的东西,都是为了离开,也许不是离开土地,但一定是告别农耕文化之路。
所谓的乡绅社会不过就是梦幻而已,就像沙坪村,就算真有乡绅的情结,那也只是夕阳下最后的一抹余晖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