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缘·烟怨

张菁 制图
我外公和我爷爷是隔壁邻居,两家相距只有几丈路,两个性格、秉性、经历迥然不同的人,“光屁股”时就是一对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好兄弟了。
外公和爷爷同样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都嗜烟如命。
外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抽烟了,那纯属是一种意外。
上个世纪初,外公读私塾后期,来了一个邻县东阳的先生,满腹诗书,为师甚严。
先生的烟瘾极大,手里常常拿着一根长长烟管。看到学生读书不用心的,顺手用烟管当武器,重重地敲学生的“栗子壳”。
外公长得聪明伶俐,干干净净的,先生每次都叫外公去隔壁农户家借火,点烟。点着了,抽几口送给先生,先生吞云吐雾的抽得很是“幸福”。
先生一管烟抽得将尽未尽时,就把烟屁股掇在讲台桌上,就着余火,再抽上一管,一连要抽几管。
开始时,外公去点烟时被烟呛得泪流满面,咳嗽不止,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一两年下来,抽着抽着就不流泪了,也不咳嗽了,不知不觉竟也抽出了一种淡淡的香气、甜味来了。
后来,外公每次去借火点烟,一路抽着,烟管递到先生手里时,只剩下小半管烟了,外公小小年纪抽烟已有些瘾头了。
先生默默地看在眼里,什么也没说,只是再也不叫外公去点烟了,隔三差五地换着别的学童去点烟。
先生的烟是抽不上了,外公就到家里偷着抽家里大人的烟。
旧时的农户都是自己种的烟叶,山里人烟民很多,不少年纪大点的女人都会抽烟。
那时,每年快年终了,都会有一个永远散发着浓浓烟味的烟匠师傅,一个村一个村上门来刨烟丝,老辈们叫做“做潮烟”。
做潮烟是种极精细的技术活,乡里没几个人会做。烟匠师傅会把晒干的烟叶打匀,再一张一张轻轻地摊平,匀匀地洒上少许香油,晾干后再一张张叠起来,制成一个厚厚的方块,四周铲下的边角料掺入下一捆烟,然后用一个特制的像迷你型的榨油机一样的烟夹子把叠好的烟叶紧紧地夹住,老辈们叫做“打烟捆”。
烟匠师傅稳稳地把烟夹子骑在胯下,平心静气,用宽宽的、锋利得像剃刀一样的烟刨一下一下浮浮地刨,长长的细细的烟丝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
好的烟匠师傅靠心思和手艺吃饭。
烟匠师傅来做潮烟的那些天,是村里“吃(抽)烟佬”们的节日,满满的聚着一屋子人,品、评着各家的烟丝,一整天屋子里都弥漫着浓浓的烟气。外公和爷爷天天窝在那里。
外公长得文绉绉的,不善农事,种出的烟叶又薄又小,晒干了也是黑咕隆咚的。爷爷长得粗粗壮壮的,勤劳善良,种出的烟叶又厚又大,晒干了金黄金黄的。
爷爷种的烟叶刨出来的烟丝是乡里最好的,这是见多识广的烟匠师傅说的,别人抽了后也都很信服。
外公常常到我爷爷家去蹭烟抽,外公说我爷爷种的烟叶像烟匠师傅说的,抽着真香。
下雨天和晚上,外公就时不时地到我爷爷家,一边抽着烟,一边天南地北地谈天说地,但每次说的总是外公,听的总是爷爷。
临走,爷爷用南平纸包了一大撮烟丝递给外公,外公也不推辞,满心欢喜地走了。
有一次,外公破天荒地约爷爷一起到高高的长垄岗上去斫柴,外公没带烟具,爷爷带的烟管不小心也在山上弄丢了。
两人烟瘾发作,浑身燥热,像两只无头苍蝇似的,再也没心思斫柴了,满山满垄地找,角角落落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那根烟管。
还是外公想出个好办法,斫了一根比手指粗点的小竹子,用细硬的树枝条戳通后,现做了一根烟管。两人在山坡上懒懒地斜躺着,看着蓝蓝的天,看着绿绿的地,一口气轮流抽了十多管烟。
外公说,那次烟抽得最香,浓浓的烟香中掺和着淡淡的新鲜竹子的清香,真过瘾,那种味道是一辈子没有过的,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说好是一起去斫柴的,结果外公的柴一大半是爷爷给他斫的,也是爷爷帮他挑下来的,外公是个“书生”,没有多大的气力。
后来,外公早早地答应把美丽善良的大女儿许配给爷爷朴实勤劳的三儿子,他们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和父亲,破了我们村一直不成文的同村不通婚的老规矩。
不过外公没有福气,没有挨到我母亲和父亲成亲的那一天。
外公后来得了肺病,一直咳嗽不止,慢慢地竟咳出了一些血丝来。再后来,抽了大半辈子的烟也硬生生地戒掉了。
外公要走的时候一直闭不上眼睛。弥留之际,目光幽幽地游来游去,看着身边的亲人。看到爷爷了就定定地盯着他,想开口说话又没力气说了,只微微动了动嘴唇。
爷爷听懂了外公的心思,默默地装了一管烟,点上火,吸着了,双手轻轻地把着烟管,缓缓地送到外公的嘴里。
外公弱弱地只吸了一口烟,抿在嘴里,再也没有张开。
外公把那口烟咽了下去,安安详详地合上了双眼,大大的两颗热泪滚落了下来。
外公入殓时,枕头边放着我爷爷送的一大包上好的烟丝和一根擦得金光雪亮的铜烟管。
爷爷从此也戒烟了,活到七八十岁也再没抽过一口。爷爷说,外公走了,一个人抽着没有味道了。
爷爷还说,外公的命是烟抽没的,我的好心好意也害了他。
外公走的时候是1948年的秋天,距今整整六十年了。那年他只有五十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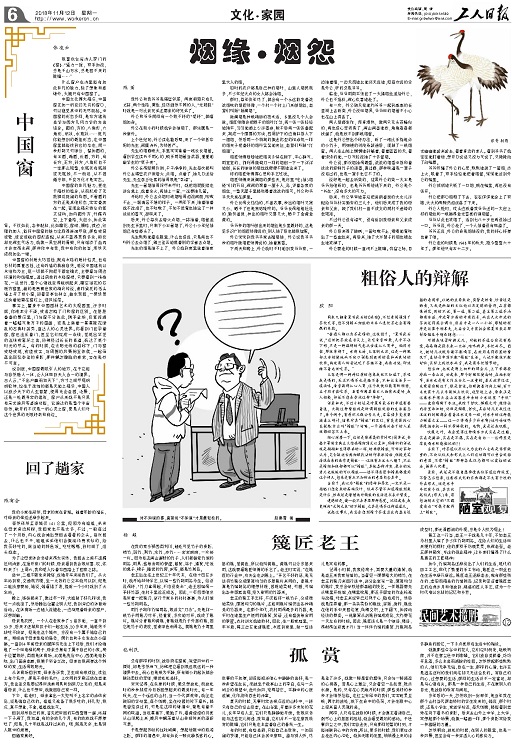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