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春秋流转,人世飘零,子女们从史料和日记捡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也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两代人的东京审判

庭审现场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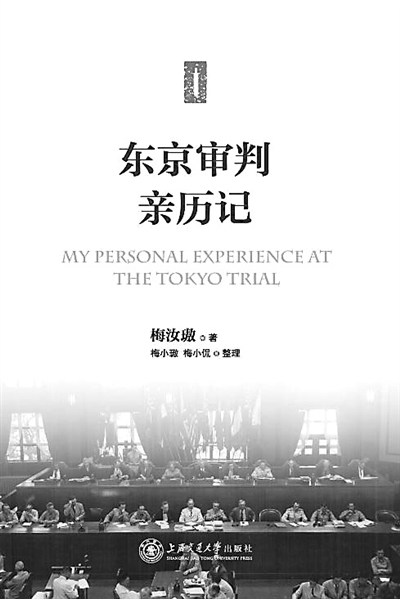
《东京审判记》书封
10月19日,《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全球首发。
图书出版距东京审判宣判68周年的纪念日不足一个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庭,开庭817次,在1948年11月12日作出宣判。
当年的审判,因地点设在东京原陆军省大楼,故简称为东京审判。
70年春秋流转,人世飘零,目前尚健在的、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高文彬已95岁高龄。
有很长一段时间,国人对东京审判所知不多,即便是当年中国代表团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濬,也很少对子女们描述过他们亲历的那场世纪审判。直到他们谢世若干年后,子女们才从史料、日记中回溯到父辈那段峥嵘岁月,捡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也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少言”的父辈
梅小璈1952年出生的时候,梅汝璈已经48岁了。从年龄上看,“中间隔了两代人”。散淡平和是这位“中国大法官”生前留给儿子梅小璈最深的印象。梅小璈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与父亲共世的21年,父亲留给他的记忆并不鲜明,小时候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
向哲濬和儿子向隆万的年龄差也有49岁,父亲亲历东京审判时,向隆万年仅5岁。如今,向隆万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致力于东京审判历史的发掘、研究。他也很少听到父亲说起过那段经历。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向隆万说父亲“少言”。
当年,中国先后派出17名成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梅汝璈和向哲濬都是上世纪初清华学堂的毕业生,又都从美国名校留学归来。他们代表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走上法庭。
建国以后,梅汝璈任职外交部,向哲濬在上海多所高校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两人晚年平淡,很少说起那段经历。
只有一次,梅小璈听到父亲在家里说英文,是父亲的朋友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到访。“他俩就坐在藤椅上,用英文交流。”
向哲濬晚年,一位知道经历的老师曾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大法官有多大?”
他微笑作答:“代表国家啊。”
两人先后与1973年和1987年离世。
对父辈的“再认识”
后来关于父辈与东京审判的历史,来自于他们对父辈的“再认识”。
2005年,讲述东京审判的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的编导在上海找到向隆万,问了一些父亲和东京审判的问题,但他却“一句也答不上来”。这令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学教授十分惭愧。第二年,这惭愧又增加了几分,故事片《东京审判》来沪首演,面对记者的提问,向隆万仍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决心去探求父亲和那段历史。
2006年,向隆万利用出差机会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看到了近40卷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的微缩胶卷,还看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版的纸质庭审记录,每4页被缩印在1页上,共计20多卷。同年,他再次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翻拍了一些照片文字。
不过,对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向隆万认为,“内容都很单薄”。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进修,当他知道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也有纸质庭审记录时,2007年,他利用到美国探亲的机会,到该图书馆复印相关资料。根据索引,他共找到父亲向哲濬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0次发言,庭审记录100多页。
这些史料,让向隆万走进了一段父亲的人生,也开启了他自己的一段人生。两者都是他此前陌生的。
梅小璈了解到父亲与这段历史渊源是在1985年。当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有记者要写梅汝璈的事迹,来梅家采访。整理资料时,众人发现一捆被旧报纸包裹得整整齐齐的稿纸。稿纸上是梅汝璈未竟著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前四章。和稿纸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几本日记,记录的是1946年梅汝璈被委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之后,从上海到东京参与工作的日常。
史料和日记里有另外一个父亲,与印象中的不同。
“另一个”父亲
日记里的梅汝璈是这样形象:他和国际友人谈笑风生,吃西餐,说英语,也时不时回忆起自己当年的留学时光。
梅汝璈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只剩下东京审判期间残缺的几本,其中大部分日记在动荡的岁月里遗失殆尽。
“他在日记里观察日本民众的精神状态,担忧国际形势的变化,担忧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更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父亲满怀忧国忧民的情绪,常常到了夜里两三点都不能入睡。”梅小璈说。
日记里的父亲还是浪漫的,梅汝璈在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写下:“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日记中的父亲,并非儿时记忆里那么散淡和无欲无求,“他的内心是汹涌澎湃的。”在父亲去世了几十年后,梅小璈这么说。
而向隆万对所收集到的父亲的讲话进行整理翻译,于2010年出版书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书中涉及大量一手资料,在当时的国内罕见。这开启了这位退休数学系教授的东京审判研究生涯。
在历史的回溯中,向隆万对一些疑问也有了答案:向哲濬在青少年时期,曾在衣襟上手指血书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与同学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所以,他成家较迟,向隆万比父亲小了49岁。
梅小璈说,父辈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人。
父辈的回声
在对父亲并不多的记忆里,有一个父子相处的小故事,梅小璈和姐姐都记得:小时候他们住的平房老旧,屋子内中心部位加了一个立柱。梅小璈有一次看完小人书《西游记》,说那根立柱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第二天醒来,他发现柱子上多了一排小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字是梅汝璈写的。
在平淡如寻常人的生活中,梅小璈和向隆万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父辈舌战法庭的壮怀激烈。
法庭上,曾发生过法官和国旗的位次之争。最初,中国法官排在英美之后,梅汝璈经过与各国法官的唇枪舌剑,甚至不惜以脱去法袍的方式抗议,终于为中国法官争得了合理的座位。中国国旗也自1840年以后,第一次在列强参加的国际活动中居于首位。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则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当年的审判,苏联代表团70多人、美国代表团100多人,美籍日籍辩护律师130多人。17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人手奇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殚精竭虑、团结奋战,在东京发回的电报中,他们分别用“在事各员昕夕从公,未敢懈怠”和“职责所在,自必全力以赴,决不疏怠”表达决心和意志。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最后宣判前,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死刑存在不同看法,只能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投票前,梅汝璈法官做了最后陈述:“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时隔70年,这历史的回响仍然掷地有声。
两代人的汇通
70年后,作为父辈的高文彬仍在为东京审判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发出倡议的还有梅小璈、向隆万等当年东京审判亲历者的后人。
梅小璈说,父辈有一个中国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法庭上的一切行为严格遵循了法庭的要求。当年的审判遵循英美法,所有被告先无罪推定;检方必须在检察阶段提供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并以事实和法理驳斥辩方的无理证据,法官才能据此在量刑阶段进行判决。
大料的史料研究,让向隆万相信那是一场“文明的审判”,历史驳斥了“胜利者审判”的说法。他说,东京审判必须得到捍卫。
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全球唯一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向隆万是中心的名誉主任,梅小璈等当年亲历者的后人也参与其中。
5年来,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合作,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的中文版《东京审判研究文集》便是该中心于2011年出版的,向隆万为该书作序。
而在今年,由梅小璈整理出版的梅汝璈遗著《东京审判亲历记》一书的封底上,他印上了父亲那句曾被广泛引用的名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如今,梅小璈和向隆万也年事渐高,东京审判不仅定格了父辈一生最光辉灿烂的时刻,而且还像一根纽带,让他们进入父辈的人生。
如今,他们也都投身于东京审判的发掘和研究中,他们为此而奔走、著述。
于是,在这场审判中,两代人的生命也交汇贯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