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负担重、精神压力大、收入不满意成医生转行三大主因,相较于高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上的紧绷,医患关系的紧张更让从业者纠结——
【焦点关注】留?“就像一台机器,开工了就停不下来” 走?成功转型是个案,或还要缴纳培养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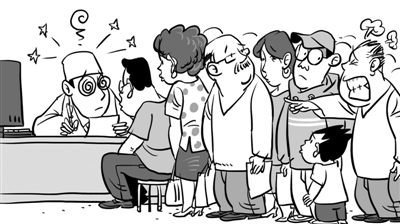
漫画 赵春青
“抱歉,刚刚着急给一位病人清洁‘造口’去了。”4月26日晚上11点左右,记者再次接通了张宇宾的电话。这位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北大医学部的大男孩,从去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某附属医院普外科工作到现在只休息过两个周末。相较于高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上的紧绷,患者和家属的不理解更让张宇宾感到纠结。
在这位年轻医生纠结的背后,是整个医疗行业对医生职业保障以及医患关系的集体焦虑。日前,某医学专业网站发布的《2015医生流失情况调查报告》指出,作为医疗资源核心的医生,近年来在我国正呈逐渐流失趋势。
该调查报告显示,25~35岁的“80后”医生是离职主力军,比例高达65.5%,其中不少为三甲医院骨干医生。从转行后的职业选择来看,多于三分之一的医生不愿再从事和医药相关的工作。“工作负担过重,缺少休息时间”,“对收入情况不满意”,“工作压力大”等成为医生萌生转行想法的主因。
普遍疲劳的状态:
“就像一台机器,开工就停不下来”
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麻醉科一位26岁女医生在夜班后猝死;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一位28岁男医生在持续1小时胸外按压抢救患者后逝世;安徽广德人民医院一位35岁骨科医生因长期加班猝死手术台……张宇宾告诉记者,每次看到类似的新闻,母亲总会第一时间给自己打电话嘘寒问暖,“电话里的刻意回避,恰恰证明了她的紧张”。
在张宇宾看来,永无休止的工作“就像一台机器,开工了就停不下来”。他解释说,像自己这样的培训住院医生,一天工作24小时,通宵夜班后还要接着上白班。“一些同事一天的门诊量就有七八十人,这在国外是一个医生一周的接诊量。”张宇宾告诉记者,经常性的“白+黑”,让医生普遍处于疲劳状态,“还不到30岁,心电图就开始出现心律不齐或者ST段改变。”
“最缺的是一个懒觉。”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专业的研三学生刘薇薇已经提前感到了工作压力。她很清楚,刚入职的青年医生基本会被写病历、查房、值班等工作“淹没”,资格老一点,发文章、评职称等晋升压力又将接踵而至。
拥有51万粉丝,微博认证为“小儿外科裴医生”的裴洪岗因为文章《我辞职了》而广为人知,他曾这样记录自己一天的工作状态:“今天又快看了近100个病人,累。值完班刚眯一小会儿,一个电话打来“抢救”,立马跳起来,就往外冲。手术间隙,就近找个地儿靠着趴会,感觉好很多。”
在裴洪岗离职的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钟山曾向媒体提供过这样一组数据:2015年我院共完成门诊、急诊量187万人次,出院病人5.7万人次,住院手术量2.1万例。而全年该院在岗的执业医师仅351名。
自我保护的防线:
病历越写越长,检查越做越多
相较于高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上的紧绷,患者及其家属的不理解更让张宇宾和同行们纠结。
做了30多年儿科医生的北大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医生丁洁,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向患者家属通知“坏消息”时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说出“红斑狼疮”几个字后,孩子妈妈立刻低下了头,我看她要哭就想劝劝,结果一难受自己先哭了,那个家长反倒开始安慰我。“那时的医患关系就像家人一样。”她感叹道。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无锡一位青年男医生因为换药问题被一位患者家属关起门来暴打。看到网络上满脸鲜血的医生照片,张宇宾很揪心,一天都不自在。“也许下一秒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他顿了顿说。
“等我有钱了,配个保镖防医闹,配个秘书写病历,配个律师审病历。”这样的桥段,常能在医疗从业者的朋友圈里看到。事实上,调侃的背后恰是医生们被击中的痛点。在裴洪岗看来,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下,病历往往成为医院和医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防线。无奈之下,病历越写越长,医患间的沟通时间却越来越短。
对医生和院方来说,同样有“防身”作用的还有本可避免的检查。“能做检查尽量做,做了CT又做核磁共振,防止发生纠纷时扯皮。”持续关注医闹问题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教授温建民无奈地说。
“一些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生极度不信任。”张宇宾解释说,以发热症状的病患为例,给他验血,病人会抱怨“简单的感冒都要抽血”;不抽血,又会有病人家属指责“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连血都不验”。“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感觉人都要抑郁了。”他苦笑道。
走还是留:
转身离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3年之后又3年”,这是在医学学生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张宇宾表示,自己所学专业属临床型,读书过程中规范培训、专科培训同步进行;然而,一些科研型医学专业,3年硕士加3年博士,还要再积累五六年临床经验才能正式上岗,“等真正成为医生都30几岁了”。他感叹,虽然“高配置”未必能带来高收入,“可真要转身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薇薇认同张宇宾的观点。据她了解,在北大附属医院系统,外校学生很难进来,即使是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毕业时也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能通过转博考试,而在博士毕业后,只有约6:1~6:2的比例能留下。“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哪能说走就走。”她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一位几年前从北大第一医院跳槽去西安杨森药业担任部门总监的师兄回校办讲座,还在宿舍引发了关于医生离职的讨论。“可成功转型的毕竟是个案,更多人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刘薇薇说。
事实上,一些医院已经在设置“硬门槛”防止医生流失。据了解,早在2014年,广东省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印发了一份《关于我院专业技术人员辞职、离职的管理规定(暂行)》作为今后向离职员工索要“培训费”的依据。规定明确:“取得执业资格证的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必须在我院再服务10年以上。未满10年者,按未完成服务期以每年3万元的培训费累计缴交还院方。”
“医院培养一名专业技术人员,要投入大量成本,人员离职势必会对医院医疗服务质量带来损伤。并非不允许医生离职,而是从保障公立医院公共利益角度出发,要求离职医生对医院损失作出补偿。”对于设立规定的初衷,该院医务科科长罗志雄曾这样解释。
医疗圈的人才流动没那么简单,“不是今天说辞职,明天就能拍屁股走人的”。张宇宾告诉记者,目前许多医院出台了关于离职的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同层次人员的赔偿金额,一些三甲医院,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离职需缴纳培养费50万元。
“有名气的医生一旦辞职很容易成为舆论焦点。出现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医疗专家辞职离开体制的很少。”长期专注医疗问题的华医网作者吴帅认为,尽管现行医疗体制下存在医生的劳务价格被硬性压低、医患矛盾突出等一系列问题,但作为个体的医生,要脱离这张“大网”很难。“如果医生群体的职业认同感持续走低,优秀人才纷纷流失,最终受损的将是全社会。”他说。(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宇宾、刘薇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