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萸·杏树·国槐
茱萸是一种树。我最早知道它,是读了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诗句。我再次知道它,是看了地方志,知道家乡的大洞山曾叫茱萸山,山上建有茱萸庙,盖因山上曾漫山遍野生长着茱萸。也因此,王维的这首诗被传说在此而写。我能想像,九月九日那天,人们头插茱萸枝,扶老携幼焚香许愿登高远望的盛景,我甚至都已感受到了他们的呼吸。大洞山曾是一座多么热闹的山啊。
高高地,在人之上,是很多人的愿望。大洞山海拔361米,是徐州市的最高峰。清明、重阳、春节,上山的道路,人流络绎不绝。站在山顶,居高临下,极目远瞰,可以看见层叠的松柏,看见重山的紫气,看见蜿蜒的运河,看见更远处的城市,只是没有茱萸。
可惜今天很少有人去想,这座山曾生长着这种望不到边的常绿树,为此我耿耿于怀。我对树木没有研究,想当然地认为,茱萸是一种带着仙风道骨的树,想当年,茱萸寺的香火是多么旺盛啊,令众乡亲敬畏感恩如至高无上的神。即或已搬迁上海的几户人家,依然乡情不忘,一度筹划斥资在原址重修茱萸庙。不过庙成,还得茱萸簇拥啊。
算起来,贾汪有人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谁来见证这段历史?茱萸树肯定比我们知道得清楚。茱萸不仅是树,也是一部历史啊。若没有茱萸,大洞山恐怕要大打折扣,它是它历史上耀眼而坚定的灵魂所在。我怀念茱萸的心情忽然很迫切。它们是在哪一年哪一天,从这座山上集体撤离的呢,是因了什么原因?它们高大、安全的住所还在,它们头上的天空一样阴晴交替,白云缭绕。站在大洞山顶,我突然明白了:我对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就像一株庄稼长得再高也无法看清全部的田野。
杏树对我,不只是一种树木。我的村子就叫杏沃,生长杏树的肥沃之地啊。我一度为这个名字骄傲自得。村子因树而得名,可见种植杏树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村前的山和大洞山同属一条山脉,一座山头一座山头数过去,不过相隔十几里,隔山相望,此杏树肯定是见过彼茱萸的,两树遥相呼应,你花开罢我花开,装点了多少人的心胸。花罢,你结果子我结豆,一个美了人的口腹,一个辟了人间的邪气,一样地被人珍重。如果有人写武侠小说,这绝对是最好的背景,剑气如虹,花落如雨,美不胜收。
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包括我的兄长,都曾种过杏树。我小时也目睹过漫山杏花摇曳的美景,只是那时,我关心的是果。杏树不是什么名贵的树,结的果实也非珍果,且不可多吃,容易伤胃。对我,日积月累,内涵深厚,成为我所关心,熟悉,怀念和珍藏的财富,最终的朴素无华的财富。这几年,它们也渐渐淡出视野,留下种果树的传统,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大洞山的山脚、山坡,山南、山北,到处生长着桃树,石榴,山楂,它们填充了我没有杏树的内容,我一遍遍看山,看树。山高树高,众星拱月,一样的花开烂漫,一样的果香飘远,一样的名声在外,不比某些名山的真容逊色。而且名山,通常和价码紧密联系,我这人大俗,名气太大的地方,还真不想去凑热闹。
城市不由自主地向着大洞山一步步走近。路成行,树成行,这树有枝形修长的国槐,它们越来越多地被城市选作了行道树,优雅、向上,开黄色碎花,结成穗的果子,可做中药,常有人悄悄摘了去,满街都飘着一种美好的香味。我想,这树也是养人的。“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这些槐树的枝条一律向着东南方的大洞山伸展。雨落枝头,落一声清脆,再落一声明亮,声声动人如歌。树荫掩映处,是拔地而起的高楼,是休闲娱乐的市民广场,是水波荡漾的玉龙湾。原本农村,忽然城市起来。
几经周折,我将家安在了槐树拥抱的一座楼房里。“父母在,不远游。”山在,树在,我没有落在其他的地方。我曾在一个早晨,用很长时间,呆望一株国槐在风中顾盼生姿,它们已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这块土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随便拾起一块石头就是一部历史,有多少汉画像石被收藏,成为珍品。但茱萸树上的淡淡香气,杏树上的虬龙盘根,甚至刚刚栽上的国槐,将一代一代的传说,将生命的温度,散落其间,庇荫着也监管着这块土地。
只要一提起这些树木,我就有一种别样的感情,我的生命像是由这些树做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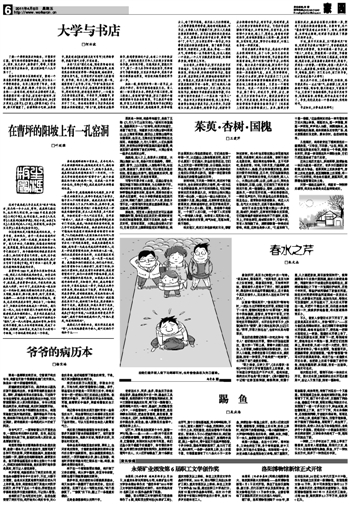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