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世纪的忏悔
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完了32万字的生态散文《谁为人类忏悔》(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读得这么慢,是因为思绪不得不常常停下来,和作者一起去追忆,去思考,去眺望。
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忧思录。严谨的新闻视角、深入的田野调查、深沉的哲理性思考和从容的散文笔调融为一体,在时间和空间的二维角度展开了一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荣衰史。有宏观的描述,也有细部的刻画。大到山川河流的变迁,小到草木虫鱼的命运,都被作者用科学的逻辑勾连起来,加以理性的熔铸,成为响彻全篇的警世钟声。
这样的阅读是沉重的。怎能不沉重呢?创造了地球上全部文明成果的人类,却在最近的一个世纪内变成了对这个星球最危险的破坏性力量。当弓箭换成自动步枪,斧头换成动力强大的油锯,徒步换成风驰电掣的车轮,一切就开始加速。淘金、砍伐、垦殖和猎杀的效率以几何级数扩大,而人们依然像温水中的青蛙,贪婪着眼前的舒适。
其实,在离我们这一代人还不太遥远的那些世纪里,亡羊补牢还有着充分的机会,然而时机被一次次耽误。等到生态灾难频频逼近,问题已经严峻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作者写道: “1998年发生在长江流域的那场大洪水,震惊了全世界。面对滔滔洪水,我们对长江的依恋和赞美好像已变成了一片诅咒。其实,长江何罪?假如长江流域那茂密的森林植被保存如初,假如早些年对长江流域的森林全面禁伐,假如没有那年均6亿吨的泥沙滚滚而下,那场洪水从何而来?”
可是,孽果已经造就,时光湮没了历史。今天,谁去问责,又向谁问责?
芸芸众生固然难免为眼前利益所左右,可是还有社会精英,还有智者。他们都哪里去了?要知道,他们的存在意义就是让真理发出声音。如果曾经失职了,失语了,那么今天再不该沉默。
古岳是怀着赤子对受伤母亲的痛惜写这本书的。他用忧伤的文字舔舐着大地流血的伤口,用悲怆的声音呼唤文明的回归。他深知,自己的呐喊抵御不了大千世界的喧哗。可是,他要秉持心中那一盏烛火,在世俗的风尘中摇曳前行。
古岳是个记者。一个记者,毕其一生的精力写出数百万字的新闻报道并不难,出版一两本书也不难。但一辈子锲而不舍地去关注某一个社会问题,并用永不妥协的态度去思考,去叩问、去辩解、去诉求、去奔走,把它当做神圣的责任,就是一个真正的“另类”,这样的追求将记者的职业意义延伸到更远。
长达十五六年的田野调查、长达五六年的艰难写作,尤其是书中所表露的心迹说明,古岳不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他是为了完成一个宏誓大愿而作的精神跋涉。
在一个崇尚功利、缺乏内省意识的社会风气中,古岳替人类所作的忏悔,未必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听。只要看看我们的生活常态就可知,现代人是多么善于回避沉重的话题。但对古岳来说,这并不很重要。他在烛照一个领域的同时,首先抚慰了自己的心灵,他正在抵达心中的彼岸。
一位忘记了名字的美国社会学家说过:“什么叫文明?如果一条高速公路能够为了一棵古树而绕道,这就是社会文明。”我相信,这也是古岳和我们的憧憬,尽管遥不可及,却让我们永存美丽的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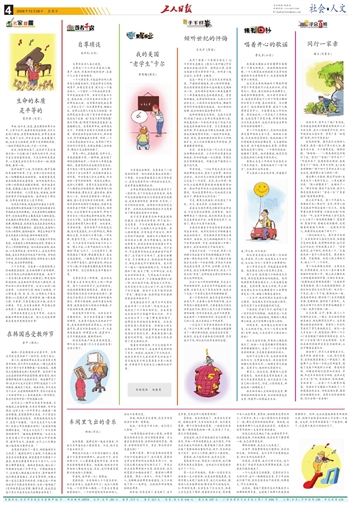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