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静思
——远亲不如近邻

资料图片
编者按
苦夏难耐。碧绿的草地上铺满了炽热的阳光,细小的喷泉虽看着热闹却丝毫不见凉意,偶有一两只慵懒的猫摇着尾巴漫不经心地走过,再就是树上那一浪高过一浪的蝉鸣、鸟儿们时而一阵的啼鸣。人站在有空调的窗前眼巴巴地看着外面大好时光慢慢溜走。可不是吗?经过了干枯的冬和短暂的春,好不容易迎来生机勃勃的夏,却被挡在一墙之外。于是闭上眼睛,任凭热烈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脸上,开始回忆……
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夏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童年的玩伴、童年住过的大杂院、童年的街坊邻里。和此时清凉安静的空调屋相比,那时的夏过得更苦,却能勾起很多人快乐的童年记忆。冯骥才说:“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苦,原是生活中的蜜。”原来这长长的苦夏里饱含着生活的哲理。本期选编两篇有关童年的回忆,城里的、乡村的,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知音难觅。
大杂院的记忆
陈桂忠
唤起大杂院的记忆,源于一个亲身经历,也颇有嘲讽意味的笑话,参加一个群的年终庆典活动,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好生面熟。此人也大概和我有同感,多打量我几眼,中午聚餐,座位相邻,一番交谈,不禁彼此哑然失笑,原来是在楼上楼下住了六七年的“芳邻”。怪不得眼熟,但以前见面,都是擦肩而过,点头打招呼都少,没有问过彼此姓名,更没有喝茶串门的经历。
要是六十上下岁的人,很多人会说:哦,我的童年,是在大杂院中度过的。
顾名思义,“大”而“杂”,是大杂院的内涵。我家住的大杂院,原本是个完整的四合院、有5间正房、3间东厢房、3间西厢房,有影壁墙,门口还有高台阶、门楼,门楼前原来还有一对石狮子、上马石,听说新中国成立前是大户人家私宅,后来家道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充公,遥想当年,是很气派的。
因为和另一个大杂院相通,这整合后的大杂院,住着13家房客,多数一家只有一个职工,养育四五个孩子,5间正房住两户人家,各住两间,中间那间是公用的厨房和过道,俗称对面屋,厢房是3间格局,也是对面屋,分别住两户人家,房租每月才三到五元钱,类似当下的“廉租房”。男主人上班养家糊口,女的操持家务。每家都好几个孩子,七八口人挤一个大炕。院子本来狭窄,邻居们又在自家门前纷纷搭建起煤棚、高灶、厕所、猪圈,有的老太太养鸡,还用秫秸在自家院落夹上“杖子”,原本就不算宽敞的庭院显得零七八碎、拥挤不堪。
由于杂居,各家灶台钻出的气味,满院子人都可以闻到。哪家夫妻吵闹起来,满院子人竖着耳朵听。大院子人家多,孩子自然也多,十来岁的孩子成天疯玩,爬树、用弹弓子打鸟、下河游泳,藏猫猫、堆雪人,女孩子聚在一起跳皮筋、踢毽子,玩的昏天黑地。
夏天闷热,逼仄房屋呆不了人,家家户户搬出板凳、蒲团,坐在大门洞台阶上。男人穿着短裤,端着搪瓷茶缸,摇着蒲扇,谈天说地。家庭主妇们哧哧地笑着,一边纳鞋底,一边议论家长里短。
院子里姓王的哥俩很有“文艺细胞”,喜欢吹长笛,常常夜深人静中来一曲,《扬鞭催马送粮忙》分外欢快,《牧民新歌》分外悠扬,我听得如醉如痴。院子里还有个孙姓哥们,喜欢哼哼样板戏,时不时吼上几嗓子。他没有文化,拿不准歌词,如:“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轻轻一抓就起来”,经他一唱,就变成了:“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哈哈一笑就起来。”一张嘴,常常笑倒一片,满院子人敲窗户喝倒彩。
大杂院住着的人都不富裕,每次收取电费的人过来,妇女们都要讨论半天,谁家点得灯泡度数大,谁家经常睡觉不关灯,为多出的几分钱电费争吵得口干舌燥,也偶尔因为发现自己家的母鸡下的鸡蛋落到别人家鸡窝而争执。但多数时候,大院是祥和的。下雨时,哪家没人,院子里的衣服保准有人替收起来。有个沈姓孩子,刚会爬的时候,母亲出去了,他在炕上爬来爬去,正好地上的铁锅里熬得米粥滚热,他一头扎进去,哇哇直叫。幸亏同院的王奶奶听到哭声,颠着小脚把他捞起来,捡回了一条命。大院里有几家养猪,每到杀猪的时候,总要熬上一大锅酸菜白片肉,打发孩子,用一个大海碗,各家盛上一碗,恭恭敬敬送去。
大杂院人重情,这些发小,情如兄弟。搞了对象,第一个告知的,多是大杂院的同伴;结婚以后,还是相互惦记。一旦哪家老人故去,那些抬棺木的,多是大杂院的哥们,神情肃穆,这就是情,这就是义。
五十多年过去了,往昔大杂院的同伴有的远走他乡,再见面,乡音未改鬓毛衰,错愕之间,相互认出,欷歔不已。大杂院旧址,早化为高楼巍峨,但我时常在梦中回忆起青砖黑瓦白粉墙,嘈杂拥挤而又淳朴温馨的大杂院,那面目慈和的老奶奶,在一起疯跑的同伴,那是一种温暖又踏实的感觉,现在已经稀缺难觅了。
那些年一起玩的小孩
陈重阳
老街坊是被土地和绿色所拱围的。土墙土路,灰色的调子,却不沉闷,有高大的刺槐、泡桐、苦楝等树木簇拥着。午后太阳筛下斑驳的碎金,绿荫匝地,时光恬淡而悠然。
老街坊里的小孩,不上学的时候,就一拨儿一拨儿像游神一样瞎溜达,东家西家串门子,从不认生。我和俊生去国宝家的小卖铺看稀罕,我胆小,他和我不一样。俊生趁国宝爹转身的工夫,抓过一把青盐,装在口袋里。我看得真切,他朝我挤眼,我便没吱声。
俊生家的三间大房子半夜塌了,幸亏及时逃命。他父母出外讨生活,留下俊生和他姐姐,他姐姐只会做夹生饭。没有菜,只好白饭上散点盐来提味儿。但后来,俊生家生计好了,没有再手长去偷东西。这件事我一直替他保密。
健魁是个捣鸡毛,不爱读书,天胆儿,专惹是生非。他放学时腋下夹着崭新的课本,却是做样子,根本没翻开过。健魁二叔说:你要好好学习呀,将来混个人模狗样,吃公家饭。健魁不以为意,脖子一梗:你早知道这,你也不会敲土坷垃了,还好意思说我呢!他二叔被噎,悻悻而去。
健魁对汽车感兴趣,我和他一起去公路上看过汽车。他看见汽车踩着大胶皮轱辘呼啸而来,就跟中了邪一样,眼神愣愣地死盯。健魁自认不是读书的料子,果断辍了学,把一大摞复习资料都送给我用,他后来果真当了司机。
迎新个子高我一截儿,12岁便会骑马。他祖父早先是赶大马车的,他应该是继承了这种基因,对枣红色的大马,不生涩,不怕马尥蹶子,翻身一纵就跳在马背上,哒哒哒在巷子里跑。他老嫌马跑得慢,嘱咐小伙伴在后面用柳条儿抽马。马疼了,就腾起蹄子一路嘶鸣狂奔。
我曾央迎新给我拽过马鬃毛。马鬃毛细长,结实,挽个活套儿结在一根竹竿上,可以套青蛙。青蛙在村池塘的荷叶上呱呱歌唱,颇有“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气势。但一有响动,贼机灵,扑通就跳下水隐身了。我极小心,竹竿慢慢靠近它。在它得意之时,套儿靠近它头部,猛地回收,便牢牢套住了。逮青蛙纯粹是玩,并不杀生,放盆子里看它游泳。最后把它放进自家的稻田里,让它守护稻子。
占生这个娃爱读书,是大人们口碑中的典范。他一直闷在家里读书,连走路也低头看着脚尖,仿佛是在思考复杂的问题。占生因此曾经碰壁,把头上磕个大包。他母亲用手研磨着,吹口气,心疼地叨叨:可怜我娃,将来一定要读出功名来。
村子里放露天电影,千载难逢呢。我喊占生去看电影,占生呆家里就是不出来。没办法,我只得自个儿去了。他是书痴,真把书读进肚里去了,后来真成了博士,在外面混得不错。很多年没见了。
老街坊里的小妮子们,翘着小羊角辫儿,脸蛋儿都红扑扑的,很文静听话。她们在巷道里跳格子,或者是抓石子儿。男孩子们俯冲过去,会故意踢飞了她们的石头子儿,或者冲撞了她们的游戏。她们也不甘示弱,就破口大骂。骂人的方式就是喊男孩子他爹或是他娘的名字。名字很金贵,被喊出来,仿佛就受到莫大的侮辱似的,会对男孩起到震慑作用。然而有时候并不奏效,一次小巧骂三尖子,小巧长得很水灵,伶牙俐齿不断地叫着三尖子他爹的名。三尖子急了,说喊就喊吧,谁的名字也不是在箱子里锁着的。哼,怕什么!
小巧一连串叫了百十遍。三尖子不愤,顺势在刺槐上逮了一条毛毛虫,摔在小巧身上。怕虫子是所有女孩子的软肋,小巧一边扒拉一边跳着脚,哭了起来。三尖子的母亲很是生气,抓起一支笤帚疙瘩就追打三尖子。三尖子跑到池塘边,扑通一声跳水里,使了一个憋气,潜下水去。他母亲在岸上干着急没办法。
小巧我已经20年没见过她了,听说她弃俗入了佛家,至今单着呢。而三尖子有些命苦,外出务工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命没了。多年前的恩怨,小巧一定原谅他了吧。
光阴就像一个镜头在推移。过去的玩伴儿,现在在全国各地不同的角落,也都有了各自的人生。老街坊里,断墙残垣,一片荒芜,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时光已经淹没了所有的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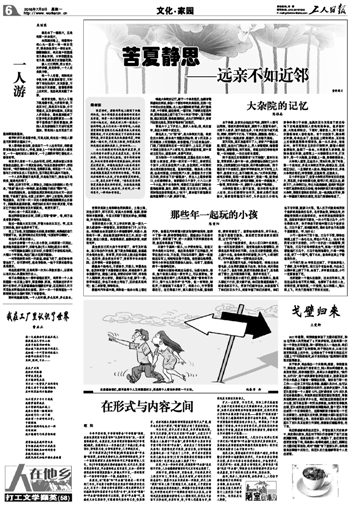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