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骼与肌肤:历史的真相与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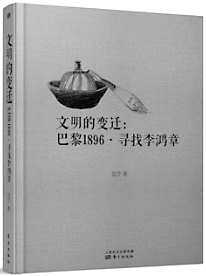
前不久,媒体人郑若麟来我家喝茶聊天时,带了一本他的夫人、作家边芹的新书,《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话题说的是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出使欧洲的事情,作者没有故作高深,文字也清晰直白。阅读这本书时,读书一向很快的我,忍不住冒出“一定要慢慢品味”的感觉。
李鸿章当年出使欧洲访问法国的细节,在中法两国的官方档案里罕有记载,当事人、亲历者留下的文字也很少。边芹为了此书,付出很大努力,实地走访了李鸿章当年在巴黎活动过的地方,线索主要来自一百多年前法国巴黎的旧报纸。其中有些实地是真的,例如李鸿章到达的火车站,下榻的大饭店,吃饭、看马戏的埃菲尔铁塔95米高处,与总统见面的爱丽舍宫,甚至还包括乘马车行走过的街道。这不禁让我想起,数百年前,有个欧洲人带着《荷马史诗》,在荷马史诗提到的每个地点走访,就地阅读。这叫“行万里路,读一卷书”。
当然,不管是欧洲人实地阅读《荷马史诗》,还是换成中国人来实地阅读《史记》,都会面对一样的问题: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没了,有的明确,有的模糊。无数的历史就像是考古发现的遗骸,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基本只是一具骨架,要让历史完整地丰满起来,需要为它添加肌肤。对于历史的感觉不会凭空而来,当边芹讲到李鸿章在法国总统府的活动(也就是今天的爱丽舍宫)时,它的历史——从国王到国王的情妇,从将军到银行家,从仓库到革命者——会逐渐清晰缓慢地流淌出来。这就是我们从作者书中读到的“历史的肌肤”。
历史的遗骸是骨骼,人们用感觉将它生动起来,但这是否会违背历史的真相?我认为,这种说法基本都是骗人的。当你读一本历史书觉得枯燥,常常是因为它只有骨骼,没有肌肤。除了像考古报告一样的历史资料汇编,任何呈现在人们面前“完整”的历史,都是主观的,都是由感觉给其添加了肌肤的,甚至是添加了服饰、口红、发型、粉底等整套装扮的。你若觉得枯燥,常常是因为主观包装的庸俗乏味。
哲学只是神学的婢女,历史只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些跨越漫长岁月的名言都是同一个意思。所谓神学就是一个宏大的情感。对于历史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情感对于理智的影响。我们永远不该忽视情感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真相的巨大扰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接受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当你接受了别人添加的历史肌肤,某种程度上等于你接受了别人的神,被别人的神洗了脑。那么,边芹本人在这本书中的历史感觉是什么呢?我认为,她所添加的这种感觉,完全可以看做对欧洲历史既有装扮的挑战。举个例子,李鸿章出使欧洲时,带着自己的厨师还有下蛋的活母鸡,为的是有新鲜的鸡蛋吃。听起来有些滑稽,但是,当我们联想到如今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时,都是自己带着全套吃喝,你对于法国报纸当年对两只漂洋过海的白母鸡的揶揄嘲讽,是否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边芹在书里重复了一句话:文学已死,这的确是一个深刻的感觉。当我们强调对历史、对社会现实的感觉,其实认可了一个前提:感觉应该是丰富的,自由的,是让社会和历史真实生动起来的必要元素。然而,当资本社会摈弃了一切生动活泼的自由感觉,只留给我们唯一不变的金钱价值原则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否变得无比的乏味?这种被绑架、被强行灌输给我们的金钱价值感觉,不仅只在艺术品中,也在资本社会所有的文化、历史、语言描述中。它是持久的问题,直指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对资本社会最本质的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