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是生产产品的地方,也是生产乡愁的地方。它寄托着工人们的希望,也承载了工人们情感的纠结。
工厂诗歌:印记着工人的喜与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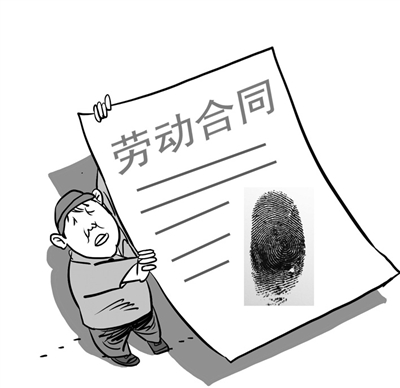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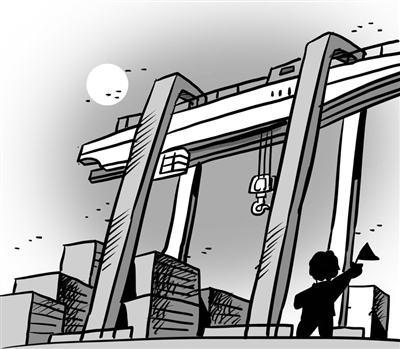
100多年前的5月1日,美国芝加哥35万工人为反对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走出船坞、车间和工厂,他们高唱着“八小时之歌”:“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厂,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后来,每年5月1日被定为国际劳动节。
工厂、车间,这个让工人们又爱又恨的地方,寄托着工人们的希望,也承载了工人们情感的纠结。
100多年过去了,世界在改变,工厂在变化,工人们的境遇也发生了无数次的变革。然而,在车间、在船坞、在井下,工人们与工厂之间的纠结却不曾改变。
劳动节前夕,《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一线工人,有国企的老职工,也有民企的新工人,透过他们的眼睛和笔触,让我们走进工厂、走进工人的内心。
想挣脱的车间
凌晨三点的玩具厂
唐以洪
这是凌晨
上帝睁不开眼睛的三点
我多想趴在厂规厂纪上睡一觉
即使不再醒来的三点
一个布娃娃从流水线的那端
无声无息跑到我的面前
仰起小小的头
停留了几秒
她仿佛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
我直了直腰杆
睡意全无
“刚开始打工生活的时候,因为枯燥的生活与森严的制度,让我感到在工厂上班就像在接受灵魂改造。在我的思维里,工厂和铁一样硬,和冰一样冷,和针一样尖利,不小心就要受到伤害。”习惯了农民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诗歌作者唐以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这位有着20多年打工经历的新时代工人在谈到工厂时,是那般地纠结。他说:“我很畏惧工厂,一直以来,在我的思想里,工厂是一个精神的牢笼,但我又必须自觉地走进去,因为我要生存,要孝顺父母和生儿育女。”工厂束缚了他,工厂也养活了他及全家,。
和唐以洪一样,曾经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做技术员(也叫机修)的李明亮,说起当年的车间、厂房,他告诉记者:“几乎每天都要一身油污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有时机器难弄,要到凌晨两三点钟,甚至天亮。”除了加班和难摆愣的机器,嘈杂的厂房是留给李明亮最深的记忆。
之所以说唐以洪和李明亮是新时代的工人,是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而言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变革中,“老工人”经历了一个从集体走向“个人”的过程,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令人羡慕的职业经过了下岗分流、再就业的重重难关,留在工厂的老工人们,对工厂的感情,有变化吗?
夜班
田力
懒得称量,三十几年他拿出了多少夜晚
用于接受煎熬,他热爱的
大胡子伯伯
在炉火中最后热了一下
就永久地凉了下去,来世,可能会去
做别人的伯伯。夜路上的夜露
叮叮咚咚响,吊着吊着就困了的月亮
掉下来,遭到了哄抢
他用自己得到的那一片儿,做成了
铁锹、铁镐,和铁锨
明晃晃,亮悠悠。他用剪子就剪出菊花、牡丹 夜来香和拉着手的小纸人
让工厂变得热闹起来
疯子从春天跑进夏天,几棵树从秋天
脱光衣裳站进冬天。白雪真白
白砂糖真甜,一滴血笨笨地
游回心脏,他也用强光手电在铁皮包装
上抓鱼
那些图案,从一个地方被运送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到了这里,那是
另一个人用另一台打签机
给他留下的记号,那一个人,他
或许也是夜班
在鞍钢工作了几十年,子承父业的老工人田力,说起上了无数个夜班的工厂,对记者说:“夜班的时候是枯燥,孤独,难捱的。为抵抗困劲,只有自己找乐,或者靠自己胡思乱想才能一分一秒地打发那些难耐的时光。”然而,想比起唐以洪、李明亮对工厂的感受,田力眼中的工厂不光是冷峻、律动、轰鸣,有时候也带有一丝温柔,他会给工厂里的机器和工具,起个别名,“比如捞渣木棍,我叫它教鞭/钢水儿如果不听话/或者戏耍先生偷懒不学习/就罚它打手板儿。比如推钢机/我叫它小推子,比如转动的蒸汽排放风轮儿/我叫它厨房油烟机,振动台总是抖/就叫它小舞子。”
离不开的工厂
手印
唐以洪
面试,笔试
试鞋一样被试用
然后在一张纸上
大拇指按下了手印
手印面色红润
端坐着,像慈善的罗汉
我暗暗祷告
——菩萨,保佑我
能把自己赎回来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唐以洪刚刚在制鞋厂签下劳动合同。他说:“当时身边的工友经常把劳动合同比喻成卖身契,一旦签订了合同,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甚至感觉思想都不是自己的了。”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在他们眼里,工厂或许是一种情感的纠结,那里能给他们带来一份稳定的收入,那里也给了他们一定的限制。打工挣钱养家,是他们进入工厂的最大愿望。
端午
李明亮
工业区的银行里
件件朴素的工衣排成长队
邮政所前的信筒里
塞满写着“某某乡某某村某某某收”的信
无处不在的网通话吧里
说着方言的外乡人一个比一个大声
超市里大红广告和精致的粽子告诉我
今天,是被外国人抢去申遗了的
中国人的端午
——在他乡,我是不吃粽子的
特别是在今天
我知道,此刻
老家的门楣上
正插着青青的艾蒿
灶屋大锅里咕嘟咕嘟的热水
正和鼓胀胀的粽子一起顶着锅盖
年迈的父母,正坐在窗前
等着千里之外的我
用一根电话线
接通灶膛边那缕缕粽子的清香
每年春节期间等待发完工资回家团圆的迫切心情、每逢过节排队打电话的心酸、每次去邮局路上握在手心里的沉甸甸的汇款单或家书……这首写在节日里的诗歌,或许更好地表现了打工诗人对工厂的记忆。
抹不去的标签
龙门吊
老井
只有在白云间往来,思想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只有把钢铁的脚挨上工厂
才可能活得惊天动地
它那么高的个子,去到地上捡起一朵落花
居然不用弯腰。几只飞鸟,惊愕地从
龙门吊的腰间飞过。在工厂
在露天货场,这工业的庞然大物
市场经济的一扇大门,柔软的手像一把
可变的钥匙,扣紧一团团工业、商业的粗粮
细面,抓取至汽车内,工厂里
硕大的集装箱,一甩过去就是白花花的银子
成捆的黑夜,搬运到船舱里就变成白天
司机坚毅的目光越过辽阔的白浪
与大洋彼岸一双幽蓝的注视相撞,高大 龙门吊
在二百米的跑道上,以一百吨的握力
把一个城市拆开,打包运走
把另一个城市卸下,在辽阔的平原上安装好
在工厂,我看到产品们
在一双大手的指引下,跳过了龙门
消失在广漠的秋空里
煤炭工人老井的这首诗,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工厂与工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时代的背景下,任凭社会变化万千,工人的手只有在工厂里才会大有可为,工人的脚只有触及工厂的地面,才可能活得惊天动地。
工厂,是生产产品的地方,也是生产乡愁的地方。曾经的辛苦,也许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唐以洪,如今已回到四川乐至,在一家电子厂上班,8小时工作制,有双休,有法定假日,有年假和产假,他告诉记者:“打工20年第一次遇到,感觉像进了天堂,心中的伤口在慢慢愈合。”
李明亮,2006年进入浙江台州一家公司,“工作环境相对更自由,快三个月了,却只写了一首诗,而且只写了一半……”他说,他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越是在底层工作、生活,越是苦、累的时候,写的诗歌也越多。因为每一首打工诗歌都是一个打工生活片段的真实记录。
田力,这个从祖父、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的老钢铁工人,还在坚持用诗歌记录着工厂里的点滴变化,他说:“一件工具有可能伴随一个工人半辈子以至于一辈子,它就像是你身边的一个伙伴,慢慢地,心里都会产生一种相互依恋的感觉来。”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工厂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印记。
(本文插图 赵春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