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家·老故事】


老树新芽枝叶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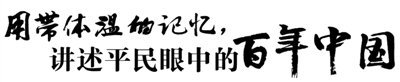
土匪的恶与霸、老百姓的怕与恨,战争的残酷与遗患,人们的苦难与迷茫,这些全都被78岁的老太姜淑梅写在了书里。60岁才开始尝试识字的她,在书中还如数家珍般回味困难时期洋槐叶子、桑树叶子、臭椿叶子、榆树叶子的不同口感,读来让人欷歔不已——
78岁的姜淑梅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这让很多认识她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60岁才开始尝试识字的她,当对身边人说出想要学习写作的想法时,除了得到大女儿艾苓(黑龙江女作家,本名张爱玲)的支持和鼓励,几乎没人认为她说的是真事。
姜淑梅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读了山东老乡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和半本《红高粱》后,琢磨着这样的文章自己也能写,但家里人觉得她只是说着玩罢了。
姜淑梅不服气,“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好故事可多了,哪一件放到今天都是稀罕事。”她使着劲儿努力为自己争口气,没想到不仅真出了书,竟还出了名。
姜淑梅说自己就像那地里的熟辣椒,老了老了,反倒红了。
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
1937年,姜淑梅出生在山东巨野县百时屯村,家里既是地主又是官户人家,然而似乎从她记事起,眼中的世界就没有安稳过。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后,她跟随丈夫跑盲流辗转落脚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20多年的家属工,随着6个儿女相继成家立业,操劳半辈的姜淑梅总算清闲下来。
想着终于可以晚年安度,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乱了生活的所有节奏。1996年9月,姜淑梅和丈夫回山东老家途中遭遇撞车,老伴儿不幸去世。心里难过时,她整夜睡不着觉,靠学着织毛裤打发时间,原本清瘦的身体没多少日子就掉了20斤。大女儿艾苓怕这样熬坏了母亲的身体,就建议她识字来转移注意力。
生逢乱世,姜淑梅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60岁之前依旧大字不识几个。凭着坚持不懈的韧劲学了几年写字后,她对自己能够“对付着看书”感到“谢天谢地”,至于后来写文章、出书、成名、上电视,在姜淑梅眼里都是“赶巧儿”的事。
姜淑梅的文章,写的多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她不懂得技巧,但下笔简单、直接,有力量。到北京鲁迅文学院看望女儿艾苓那年,她蹭过一节叫做《电影·文学·人生》的课,记住了“细节”的重要性,艾苓和同学在宿舍闲聊时说“人家都知道的事,你废话少说,要讲就讲人家不知道的事”,她也记下了。有读者感慨姜淑梅笔下故事篇篇精彩,每个字都“钉”在纸上,每个字都“戳”到心里。
姜淑梅写乱时候,多少血肉模糊的故事,在她笔下都讲得不动声色,却又恰到好处。文章读罢,土匪的恶与霸、老百姓的怕与恨,战争的残酷与遗患,人们的苦难与迷茫,全部跃然纸上,回味时总感觉嘴里泛着血腥味,心也跟着翻了个,好像一口气上不来似的那么憋闷。
雨不下了,白老鼠、猫头鹰一个也不见了,太平了,俺娘说:“这个月子过得心提溜着,今天可得好好吃点儿饭。”
做好了饭才想吃,二大爷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回来了,二大爷说:“这个胡子活着,俺给他一刀,用脚一踹,心就出来了。这才是活人心,俺吃了它!”
这顿饭,俺娘一口没吃。
——摘自《胡子攻打百时屯》
一九二七年,巨野出了两个人命案,杀人的都被点天灯了。
平常县城小,人也少,听说要点天灯,很多人特意进城看热闹,有住亲戚朋友家的,也有住店的,县城里的人一下就多了。县城东北有个戏楼,点天灯就在那个地方。
点天灯就是在犯人的两个肩上挖洞,放上粗灯捻子,倒上豆油点着,把人慢慢烧死。点着天灯,戏楼上那个娘龇牙咧嘴,大声叫唤。不大会儿,台下的人走了一半儿。
——摘自《点天灯》
姜淑梅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不觉得稀奇,她说,“战乱与死亡,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平常不过的事,我把这些写出来,只想让后世人知道祖辈都经历过什么,现在年轻人都生在蜜罐儿里。”
根是苦菜花 , 发出甘蔗芽
姜淑梅说,她能写文章、出书,全都因为摊上好老师。姜淑梅的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大女儿艾苓。
艾苓是大学副教授,也是作家。姜淑梅羡慕读书人,大女儿自然是她的骄傲。1999年,艾苓出版了第一本书,被邀请题字的姜淑梅激动得夜里睡不着,想出了一首诗:“根是苦菜花,发出甘蔗芽。本是乌鸦娘,抱出金凤凰。”现在再提起这四句话,姜淑梅觉得放在自己身上也合适,“过去日子过得苦,哪承想,俺这老乌鸦娘老了老了,要变成俊鸟了。”
封建时期的中国女性,地位卑微、处境难堪,姜淑梅置身其中自然感触深刻,所以她写得透彻,一针见血,“旧时候女人地位低,父母给养大了要嫁人,嫁人生孩子了娘家还是得一直陪送,老话儿说‘谁家生了闺女,粪坑都撅三天嘴’。”
姜淑梅一辈子没少挨累受苦,好不容易熬过了战乱,反倒是不打仗后,有几次差点丢了性命。
写穷时候,姜淑梅说挨饿那两年的事情最难忘、也最难写,写了好多天,心里难受。1954年农历5月15是她出嫁的日子。临行前,娘告诉她“到人家你得听公公婆婆的话,许公公婆婆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对,不许你一个不对。”姜淑梅直到今天也没有违反母亲的叮嘱。
“1958年搞大跃进,家家挨饿,庄里的榆树皮都让人扒干净,谷糠都成了好东西。年纪大的、身体弱的,有些就饿死了,可公婆却带着小叔走了,一分钱都没给俺娘俩留下,连着两个月,丈夫邮来的钱,他们也一分不给俺。”姜淑梅说,那时候真想抱着大儿子跳河死了算了,但又怕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坏了自己的名声,眼看着儿子快要饿死,姜淑梅决定与婆婆分家,公婆轮番对她破口大骂,但最后家还是分了,“婆婆给了俺一个勺子两个碗,还给了俺半碗杂面,总算能吃上供应粮,不至于饿死。”
其实公婆对她不好的事很多,但姜淑梅好像全忘了。公婆活到74岁,后来到东北投奔姜淑梅,一起过了20多年,活养死葬都是她和丈夫管。有人问她为啥不记恨公婆一家,她回答得云淡风轻,“都过去了,他们毕竟是老人。”
他们也许成为最后讲故事的人
有学者看过姜淑梅的作品后,称其为“民间历史书写者”。“民间的记录在中国始终缺乏,从历史学者到普通百姓,多习惯信任‘正史’而轻视‘野史’,似乎正史必字字确凿,野史定荒诞无据。书本上的历史和真实的民众完全无关,前者一副贴面,少有温度,后者蝼蚁般各自鲜活生动的记忆,似乎都可以忽略。”作家王小妮坦言读姜淑敏作品犹如“听老人”讲故事,“类似的讲故事的人将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存在的乡土已经面目全非,他们也许成为最后的讲故事的人。”
“姜淑梅叙述的故事,多发生在半个世纪前,比如她写饥荒岁月的生活,非亲历者不能言也。”作家马国兴对姜淑梅的文字尤为珍惜,“显然,带着体温的记忆,要比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更能让人接触到真实的历史。她如数家珍般回味洋槐叶子、桑树叶子、臭椿叶子、榆树叶子的不同口感,读来让人欷歔不已。”
“老人的故事讲得干脆利落,哪句话掉到地上都能摔个坑,只呈现了自己眼中的历史,反而更体现了最真实的人性。”更多的读者在看罢姜淑梅的文字后总觉“揪心”和“胸口堵得慌”,“世间还会有什么比穷与乱更加难熬,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就这样在老人稀松平常的话语中呈现,直到让人泪流满面”。
姜淑梅60岁识字、70岁出书的传奇故事更是惊讶和感染了身边众人。女儿艾苓感慨,“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学生都有这种劲头,他们得出息成什么样;如果我有这种劲头,我能出息成什么样。”外孙子李一在姥姥的影响下学习劲头十足,“当看到一位白发老人每天趴在那里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笔一笔地写作时,自然而然就会忍不住也想拼一把!”
曾经,女儿艾苓担心母亲是一本书作家,把自己的经历写完,应该也便再无文章可做,不料母亲的精彩远未结束,今年不仅完成并出版了第三本著作,还持续在写作的路上乐此不疲,“我的故事讲完了,还有大家的故事可以讲,怎么可能没事可写!”
书法、绘画:李法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