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兰:十月一日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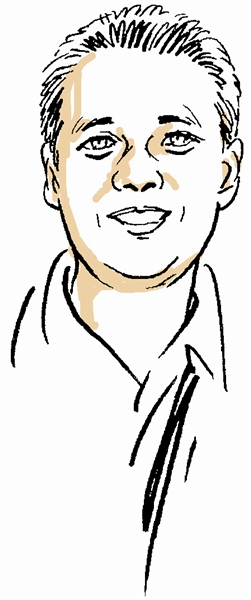
打工经历:
陈传贵,笔名,凹汉,重庆忠县人。先后从事过建筑小工、饭店服务员、操作工、机械维修工。现为高级中医推拿师。
十月的棉兰已经进入雨季。因为东南亚热带雨林气候,这里没有四季分明的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与雨季之别。当然,这里也没有国内的十月一日国庆节长假。我作为在这里已打工半年多的中医推拿师,和其他几个中国同事一样是靠拿每个客人消费的提成工资,多推拿一个客人就多得一份工钱。至于国内长假,我只有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屏来感受祖国国庆节的盛大狂欢,那些穿越千里去祖国各名山大川游玩潇洒的情景,真是让我羡慕又嫉妒。
十月一日这天一直下着雨,我只推拿了三个客人,推拿时候,有位60岁的华侨陈先生跟我聊起一个曾一直跟随他工作到退休的老员工,去年得了一场大病但拿不出钱治疗,陈先生花了20多万元把这个老员工带到新加坡去做手术。我心里特别震惊:人民币20多万元,而且都是已经退休了的员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如此善待自己的员工呢?他说自己也是吃过很多苦的人,最能体会到作为基层员工的辛苦劳累,宁可自己少赚一点,也要对员工好一些。陈先生因为年轻时出苦力引起的软组织劳损疼痛,经过我反复推拿及点刺放血拔罐等方法,基本得到了缓解与控制,所以每次推拿完毕,他都会另外付给我折合人民币100元的小费。
十月一日晚上,雨还一直下着,在秋雨淅淅沥沥的细微声中,我的烦躁与骚动骤减,减到一切都宁静下来,变得那么安详、温润。我在停电的宿舍里点上一支蜡烛,从微微的烛光中看到我自己,打工到印尼棉兰的几分孤独与彷徨。是的,我在这间12平方米左右的旧房子里已经睡了半年多。一张掉漆的方桌与一张软绵绵的单人床。失修的灰白墙皮已经开始慢慢脱落。从门缝爬进来的一只只黄蚂蚁,在灰尘满面的地上,排队搬运着腐烂变质的饼干沫与面包屑。门口上方的墙角边,一只辛勤的黑蜘蛛通过昼夜加班,把它贪婪的巨网织得越来越大,大得似乎要铺满我的整个房间,同时要网住所有叮咬我的该死的蚊子。我突然安静,很有闲情地慢慢看着蜘蛛与网,竟然感觉到这只蜘蛛就像我亲爱的女人,是在给我编织一件温暖的毛线背心,一针一线织得那么专心致志旁若无人,透出来我们在一起相爱的缠缠绵绵与炙热亲吻。在我睡觉的枕头上,从一扇小圆木的窗户飘进来一声秋雨微凉雨打芭蕉。让我想起中国是北,重庆是北,忠县是北,大巴山上无边的草木虫鸣都是北;而夜寄长安的孤人李商隐当初就把大巴山当作南方,如果是像我此刻漂泊这印尼棉兰的更远之南,一定会一剪千愁万古悠,一定会更加孤独出:君问归期未有期。让我想起这些穿过无数楼层缝隙的密集的线条之美,多么婉转而略带忧郁的乡愁,一丝丝沁人心脾的阴柔,玉一样散发出慈祥的光芒。
临睡之前,我习惯性的默念一遍《心经》《大悲咒》,并关闭空调和扯去盖在肚皮上的白色布片。我突然感觉到难得这样的一份清净。这秋雨就像浴佛节上飘满鲜花的净水香汤,在一勺勺洗净我凡俗的尘埃、污秽。我还想起了曾从中国流亡到新加坡,最后到我现在打工的印尼苏门答腊省的郁达夫先生,曾以翻译的名义掩护与保护这里的抗日文化名人侨胞,最后死于日本宪兵队的暗杀。他实际是一个文人在做间谍危险的工作,他知道危险有多大,但是为了更多的人,他早已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呵呵,我来到苏门答腊省的棉兰做推拿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比郁达夫先生的境界差了十万八千里,他才是真正涅槃圆寂,而我能够不入地狱就烧高香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