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鸡

我家门口是宝鸡。不是,是有只宝鸡。也许还不是。
初秋时去乡下高山八仙埫参观朋友鸡场,刚近栅栏,鸡们便振翅飞跑而来,“咯咯”“嘎嘎”叫个不停。我问朋友:“它们为何沸腾,打了鸡血?”朋友打趣说:“山旮旯的鸡没见过世面,人来疯,在欢迎大师啊!”大家嘻嘻哈哈,感觉十分新奇,忙着给鸡拍照,与鸡合影。朋友以为我很喜欢鸡,中秋前除送我一盒精制月饼,还有一只鸡。
这下可真犯难了,怎么处置它呢?亲手杀了它,我想,家里谁都不忍。还是先用拖鞋拴着,放在门口再说。每天给它丢些米,盛些水,不至于饿死了。
这样,门口就如市场般邋遢,每日进门出门都要面对狼狈的凌乱,忍受鸡屎刺鼻的臭味,承受由此引来的蚊蝇扰人。于是决定杀掉它。谁当刽子手呢?袁老师腰椎病又卧床了,媳妇一向怕杀鱼杀鸡,儿子整天上班家务事没沾过边,这问题就落我身上了。我早年杀过鸡,有经验,也是这个家庭应担当的人。可是我曾结交一个法师,他引我做居士时,我在众法师面前承诺过不杀生。平生信守不能欺人,更何况是无边的佛法呀!于是,我说,你们怕,我也不是浑身是胆呀。
这样,鸡就暂且逃脱灭顶之灾,幸存了下来。
正是开学初,孙子在家看小人书、上网、看电视,偶尔也玩鸡逗鸡。跟鸡说话,给菜叶、瓜果、肉食,一个星期过去,鸡便由来时的惊恐之态,变得悠然自得,不时还得意地哼唱,是那情不自禁、如鱼得水、无比舒适自满的腔调。孙越发喜爱它了。一天,媳妇做门口卫生,刚打扫干净,一泡屎尿喷到她脚上,她烦了,说:“拿到市场去杀了,一家老小感冒也好得差不多了,正好补补。”孙一听就响亮地抗议:“不!”说罢,号啕大哭。
这回只好把鸡当宠物来养了,每天清理门口,还洒上花露水去味。又想着在楼顶辟个场地,给个笼子做家,再不济也要给起个名字。小孙叫阿宝,这鸡就叫宝鸡了。给鸡的食物也变换花样了,人吃什么就给什么,一律是新鲜的。连乡下送来的南瓜、丝瓜、西瓜之类,也试着切一大块,供鸡食用。通常是食物置了一两个时辰后,孙子欣喜地叫:“鸡啄了几百个洞。”有时,孙子向我们汇报:“妈妈,鸡在拼命喝水。”
从此,鸡再也不怕人了。它由来时的惊恐、担心、害怕、提防,到如今的悠闲、适应、坦然、自如,连叫的声调也变了。不时哼唱“哦,哦哦,哦”,表示着它的无忧。一个星期后,无论谁抓它,它都不动,松了绳也不飞不跑。袁老师说鸡被关傻了,不晓得逃跑,我回说:“鸡跟你一样习惯了这个穷窝。”儿子说:“鸡被体制化了。”儿莫非是借鸡讽我?那我也不服输,就笑道:“六畜六畜,六天就熟了,有时,我怎么感觉你越养越生了呢?”一家人为这刻薄话愣住,我忍不住扑哧笑了。
鸡成了孙子的伙伴,也就使我们弃之不得。媳妇有时抱怨小孙子:“你养鸡,把妈累坏了!”可是想想这样额外的付出,能给孩子带来快乐,累点又何妨呢!孙要实现他关心他人、照顾弱小的梦,要从点滴的游戏与劳动中,收获快乐。这个,长辈没法给,鸡可以。鸡给伢的快乐,金钱无法计算,长辈呵爱代替不了,我就觉得鸡幸亏没被杀。
阳光明媚的中秋,我想给鸡洗个澡,立即受到制止。他们怕鸡感冒。月圆之夜,我们第一次与宝鸡共度佳节,赏月品饼。孙要给鸡月饼,同样受到劝止,生怕鸡食饼卡住喉咙。这样的中秋有点特别,如回到乡村般畅意。
次日,家人想到鸡太孤单,想送它到乡下,我们以为鸡比人更讨厌城市。可是孙子仍是不肯,一提送鸡就跟你急!围绕鸡的食住行,一家人常闹出笑话,给平淡生活来了点小插曲。
杀不得送不得,看来只有长留了。休假几天,孙子兴来就抱鸡去楼下院里玩耍,鸡走到哪,他跟到哪,鸡啄草,他就张嘴好奇盯着,鸡寻食,他也蹲下寻觅着。我估计鸡能很快与人熟,与它和孩子天真无邪的相处中得到的安全感有关。我明显感觉到鸡不但不再焉头焉脑,反而越活越神气了。
鸡在人的友善中活得像个艺术家,有时,我感觉它就是雀舞皇后杨丽萍。那轻歌曼舞的样子,要多迷人有多迷人。你看它单腿独立,头左扭右闪,一张好看的喙不时梳首弄姿。有时一腿独立,另一只举在前腹,张开了爪,像要梳理什么,不舍放下,一会儿又轻柔地将爪落在地上,如脚踩棉花,一边迈着猫步、太空步,嘴里还禁不住“咯,咯,咯咯咯”地唱,她是想生蛋了啊!
这只鸡注定不会被我们杀掉,也不至于被我们吃掉了。其实呢,我们天天在“吃”。用心,用手,用眼,“吃”了许多天,仍在“吃”。一家人从此获得的快乐,岂是简单一个食字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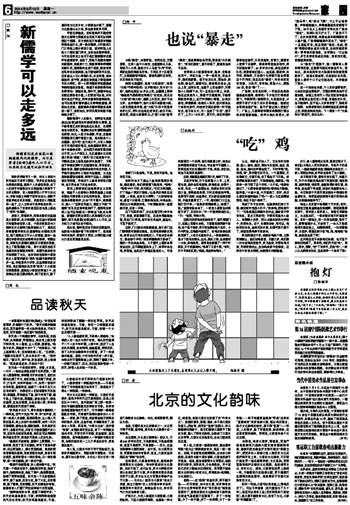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