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众相】梨园花下
忽然接到邀约赏梨花的电话时,对方手机里响着汽车喇叭声、马达轰鸣声和嘈杂的人语声,搅得那边讲电话的嗓音提到最大,我这边听着一片嗡嗡声,终于听明白了,市作协邀请一些女作家们去呈贡的万溪冲赏花吟诗。呈贡距昆明老城区几十公里,如今的昆明新城,历史上是昆明的水果蔬菜之乡,比如该地产的宝珠梨,既为朝贡之果也是本地人吃的寻常水果。上世纪末,呈贡的斗南成为国际花卉交易中心,世界各地鲜花交易所需的花,这里应有尽有。我们要去的万溪冲只有梨花,很老的一片梨树林,高寿的树龄都200多岁了,是个颇有历史的宝珠梨梨园。邀人来这样的鲜花之乡,只看朴素的梨花,开个小小的梨花诗会,是在尘嚣中发出的世外之邀。
乘中巴车前往途中,一位活动负责人向大家交代事项,反复强调切莫贪看花走迷路,她说:“十几天前我们来梨园探路,以为人人手里有手机,爱怎么走就怎么走,结果迷了路,打手机救助,问所在之处有何标志?回答:‘周围有十棵老树。’这梨园有万亩,都是百年老树,哪里没有十棵?”我默默赞赏这番以拙藏智的介绍,向邻座打听这位负责人,原来久闻其名,我记住阿芒这名儿就因为其文章里有这点东西。
出了昆明老城就是呈贡,新城犹如新人的房子,一切都很时尚,让人眼亮称奇。我们的车在老城所没有的笔直宽敞、车辆极少的大街上行驶着,一拐弯儿,开进一条仅容一辆卡车通过的山野砂石路,车行几百米后,梨花扑面,就进入了万溪冲梨园——城市已建到果园门口。车道两边的树林全是开满白花的梨树,无一杂木,放眼望去,花儿清一色的白,朵朵娇艳。树比较矮,人伸手就能够得着树腰,枝丫均匀地朝四周伸长,占了好大一块地盘。
此时园中树下没有劳作的人,赏花人也只有我们十多个第一次来的女子,还有不远不近跟着、怕赏花人被花海淹没了的诗会主持人。有“十棵老树”的前车之鉴,我们不敢由着性子来,在梨园中几步一回头,生怕走丢了;梨园中没有鸟声,也无其他声音,大家都不愿出声唤伴吵了梨园,只是竖耳静听或从白花间寻觅同伴。此时人变得像一群离岸不远的鱼,游开又游拢。跟随在后的诗会主持人张庆国,不赏花,只看掌中的手机,每一步都被花枝包围,仿佛花在看他。谁也不忍打扰他,因为他的时间特别紧——行政事务缠身,将一份纯文学刊物办得逆势而上之际再创一份作家刊物,其间所创作的《如风》还是去年全国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不把点滴空闲用上,如何能人之所不能?望着这般情形,怎不感慨:几千年来的诗词歌赋中,什么花没被咏叹?什么美景没被描述?什么道理没被说尽?人类文明的天空满当当的,前面的把空间占满,后面的快速直追,哪容人们守几亩薄田荷锄话桑麻?
一阵风起,落英缤纷,目及之处朦朦胧胧,地上转眼铺了一层柔柔白白的花瓣儿,不忍踩,又无处下脚,不得不踏花而行。情之所至,我说要写首花雨的诗,身旁一位花季作家道:“春逝伤感啊!”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见花落就有泪,活到知天命,理解了花落变泥和生命起落的必然性,想到了有的花要在霜雪中迎春,有的要在乍暖还寒的初春里探路,而后才有百花全盛的春天。说到这儿,我脑海里涌出一句诗来:“你落了/百花,才开放。”
印象中,哪儿的花开,哪里就有蜂来采。我们当中小读者们熟悉的作家汤萍发现,偌大梨花怒放的果园里,竟然没有一只蜜蜂来采花,蝴蝶也仅见一只非常普通的粉蝶。“为什么一只蜜蜂都没有?”她像个孩子似的,从清晨进入梨园一直追问到下午,大家都猜测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诗会结束前,从远地赶来与大家共进晚餐的区委周书记回答她,说有风为梨花传媒。对于这个答案,我释然了,不然在美丽的果园看人类自身的罪行,可不好受。
听说这座新城大街边上的梨园,如果不是当地人呼声强烈,区人大立法把它列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保护下来,或许它的命运同别的梨园一样,已经变成新城的一个街区。呈贡宝珠梨昆明人自小吃到老,吃了几代人,却一直没有赏梨花的习惯,所幸的是,大家终于在它幸存时赶来一赏,还有了首次的梨花诗会,值得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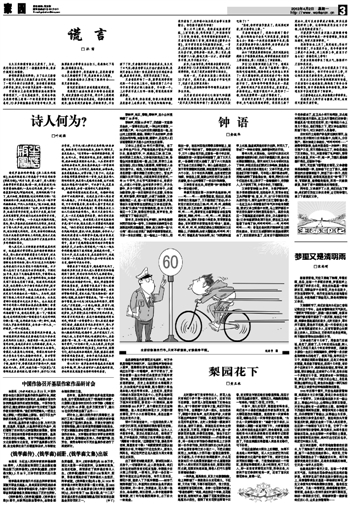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