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印记】钟语
那钟声,纯正,清晰;那钟声,在小山村里响彻了20多年。
那钟声,间隔30多年了,仍然像一支悠扬的金曲,一首绵长的山歌,一种山村的语言,一曲天籁之声,与小山村的炊烟揉捏在一起,在山村上空萦回、缭绕。那挥之不去的钟声,仿佛还在如埙吟唱,如笛长嘶,缥缈中,还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岁月里小山村发生的故事。
父亲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当了20多年生产队长,严格地说是分管生产的副队长,就是每天早、中、晚敲出工钟、收工钟,给村民派工的角儿。父亲每次敲完出工钟,沿着全村房前屋后喊一圈:出工喽,男劳力上金挂玉割谷,妇女到兔儿墩薅草,知青和老人去东边港守水。喊完,父亲拎起镰刀割谷去了,身后跟着一群手持镰刀的青壮劳力。管生产的副队长并不好当,必须是种田的老把式。一年24个节气,什么节气该种植什么,收获什么,必须心中有数;全村有多少劳力,多少头耕牛,多少个犁耙,仓库里有多少种子,必须如数家珍;每一块田地种的什么庄稼,长势如何,何时除草,何时施肥,必须了如指掌。父亲能做到这一点,但一直不愿意干这差事。只是谁当队长就非要生拉硬拽让父亲当这配角。父亲是“队委会”中的和谐典范,他20几年只做这一个工种,做得任劳任怨,有声有色,给村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年月,农村没有电声喇叭,钟声是指挥村民行动的唯一信号。父亲敲钟的韵律至今还刻录在村民的脑海里。那钟,是父亲用一包“大公鸡”烟从公社农机厂换回半截钢管做成的,不足一米长的钢管,在一端钻上一个眼儿,用铁丝一穿,挂在村后垴的那棵古樟树桩上,就成了“咚咚”响的钟了。那棵枯朽的古樟树桩子,三个人都合抱不拢;这曾是一棵千年古树,据说解放前一次雷击将树燃着了,烧了几天几夜,一场暴雨才把火浇熄了,留下六七米高没有了生命力的古樟桩子;树心全部是空的,小孩子常常围着树捉迷藏,树桩里面可以躲藏五六个小孩。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没有把它侵蚀掉。钟挂在上面,就像山村的老汉穿上合身的唐装,给小山村增添了一份古朴和典雅。
父亲没有当过兵,却把那“钟”敲得像军号一样功能分明。
早晨天亮前的第一次钟声是起床钟:咚……咚……咚……敲得慢悠悠,轻丝丝,既提示劳动力该起床了,又不能惊扰了老幼;半小时后才敲正式的出工钟:咚、咚,咚、咚,敲得既亮又激;收工的钟声,就懒洋洋的了:咚……咚、咚……咚;哪家有红白喜事催客去祖堂喝酒吃饭,则敲:咚咚……咚,咚……咚,那意思是快快、快;那年月阶级斗争复杂,常常要紧急集合,有时深更半夜要起来捉“特务”,就敲:咚、咚、咚、咚、咚,村民们便会立即赶到村口的晒场上,听候指挥;如有火警就敲:咚咚咚、咚!咚、咚!那意思是“快快快啊,快!”村民便知道带上水桶、脸盆或其他的家什出阵。时间久了,形成了一种钟的语言,指挥着村民的行动。
那年大旱,水贵如油。马对驴水库的水只能按耕地面积分配,远远不够灌溉之用,偷水抢水事故频频发生。那天本村又为水与邻村发生了冲突,年轻的后生们要求父亲鸣钟,紧急集合村民,去东港的送水堤抢水!父亲不同意,并劝阻他们不要干傻事。可年轻人哪听得进去啊,用锄头敲响了紧急集合钟。结果,两村的小伙子们在送水堤上展开了一场锄镐搏斗,伤残数人,几个被判了刑,乡邻乡亲的,不堪回首。
父亲掌管钟锤20多年,为保护那钟声,没少受委屈和凌辱。在动乱年月,常常会有红卫兵押解着“地、富、反、坏、右”分子到田间地头进行批斗。那天全村劳力正忙着收割小麦,一名红卫兵小将骑着自行车气冲冲地来到麦地,要求父亲立即集中村民,马上要押解区中学的校长高学文到村里现场批斗。高校长是这一方德高望重的教师、校长,怎么能够批斗他?父亲知道硬顶是顶不住的,便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去鸣了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奇怪的是村民听到钟声后立即四处散去,有的三五成群到竹林里抽烟聊天去了,有的回家休息了,还有的干脆到别的村子走亲戚去了。红卫兵小将不知何故,怎么喊村民们就是不回头。红卫兵不懂我们的钟语!那意思是“走走走走走呀、走!”结果批斗会上没几个观众,他们情急之下,把父亲也拖到太阳底下陪斗,对父亲进行人身侮辱。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到村口的禾场集中,拈阄儿,分田到户。那次钟是父亲敲的,“咚咚咚咚咚……”敲得非常激扬,也是村里最后一次钟声!责任田到户之后,再不用集体出工了,钟自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不久,村里安装了电声喇叭,要传递什么信息,开关一拧,喊一声,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得见,还留钟干啥?
那天,天空飘飞着零星的雪花。父亲像瞻仰英雄雕塑一样,在钟底下伫立了很久,绕着那枯朽的香樟树桩子,转悠了好一阵子,然后把那锈迹斑斑、敲得坑坑洼洼的“钟”取了下来,背回家里,擦得锃亮锃亮,再用一只麻袋裹紧,放进了家中储藏粮食的暗楼里。
两年后,父亲离开了人世,我们找出了那钟;我们把它放在父亲的身旁,让它陪伴着九泉之下寂寞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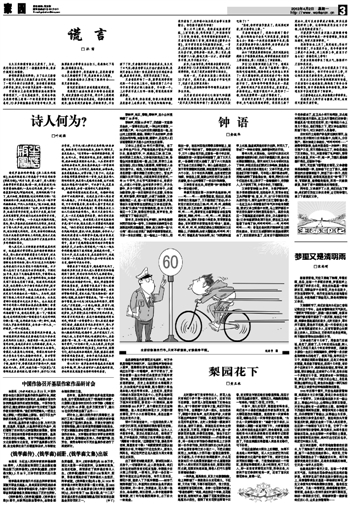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