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一种现代疾病
19世纪,法国精神病学家让·皮埃尔·法勒雷(Jean-PierreFalret)首次提出了双相情感障碍的概念。由于这种疾病会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内,出现高昂和压抑两种心理状态,法勒雷也将它称为“循环性精神疾病”(folie circulaire)。直到21世纪初,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说,这个概念才成为了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原则。
在那个时期,精神病学主要分为应激性(外界环境导致)和内源性两种精神疾病。克雷佩林将所有内源性的精神疾病划分为两大类,分别是源发性痴呆症(即现在的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双相障碍)。内源性抑郁症被归于躁郁症的范畴。当时,研究人员认为躁狂症不是由外界环境导致,便将其也划分为躁郁症。著名的德国神经病学家卡尔·韦尼克(Carl Wernicke)曾提出过反对意见,他认为躁狂症与神经高度活跃有关,而在抑郁症中,神经活动会明显减少。但克雷佩林的观点在当时占据主流,演化成了精神疾病的诊断体系。
1966年,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朱尔斯·昂斯特(Jules Angst)和瑞典于默奥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卡洛·佩里斯(Carlo Perris),分别对300位患有双相障碍或抑郁症的患者及其近亲(总人数超过2000位)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与抑郁症患者相比,双相障碍患者的近亲中有更多人出现精神混乱。同时,他们发现双相障碍患者拥有更多同类疾病的近亲,而这个发现并未出现在抑郁症患者中。基于这些发现,昂斯特和佩里斯认为,双相障碍在遗传机制上与抑郁症并不相同。
随后,在1980年第三次修订的《精神障碍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中,抑郁症从双相障碍中被区分出来。但昂斯特和佩里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抑郁症,并未涉及过躁狂症。昂斯特表示:“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躁狂症案例,无法进行合理的分析。”
双相障碍在临床表现上具有多样性,体现在患者的抑郁和躁狂的程度并不相同,发作时间也无法预测,每位患者的症状也各不相同,有时两种极端情绪还会混合出现。正如一些心理学家表示的,精神混乱包括了从抑郁症到双相障碍,再到躁狂症这个大的范围,是否需要对单相躁狂症单独诊断还未可知。
3、寻找亚种
发病症状的多样性,以及对大量精神病学基因机制的研究,暗示了双相障碍包含了多种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生理特征。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精神病学家保罗·格罗夫(Paul Grof)说:“经过50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双相障碍的理解仍然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仍然被看作一个整体,但它显然不是。”
格罗夫表示,亚型遭到抵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过去几十年内,精神病学的研究经费和工作逐渐由大学转移到了制药公司。而制药公司为了节约研发成本,通常只考虑新药的治疗效果是否好于安慰剂。显然,当用药群体越大时,新药呈现出的效果才有可能更好。
将双相障碍进行划分后,多个病症分类会使药物的疗效评估变得复杂。同时,制药行业也倾向于研究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下文简称FDA)认可的疾病清单,而单相躁狂症还不在名单中。
制度惰性也在其中发挥作用。每次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下文简称DSM)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新版本都是基于上一个版本,但任何修订都需要基于新的证据支持,并提交给FDA裁定。
最新版本DSM-5是在2013年颁布的,单相躁狂症仍被包含在双相障碍中。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家、DSM-5修订工作组的成员特丽莎·苏皮斯(Trisha Suppes)说:“关于躁狂症是否应该从双相障碍中划分出来的讨论还非常有限,因为它的发病症状和病程与双相障碍没有足够大的差异。”
单独诊断的缺乏也意味着证据难以收集。在DSM-5中,标准化的临床访谈并没有单相躁狂症的分类,这也意味着对这种疾病的调查需要依赖于特别渠道。单相躁狂症似乎面对着进退维谷的处境,缺乏单独诊断是研究的障碍,因此单独诊断也变得更不可能。
而在已进行的研究中,缺乏对单相躁狂症的准确定义使得结果很难进行比较。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学家艾伦·杨(Allan Young)说:“对单相躁狂症的‘定义’是主要的问题。”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可以根据症状的严重性和发病频率来定义躁狂症。在对单相躁狂症的研究中,一些患者有过至少一次躁狂经历但无抑郁史,而另一些研究中的患者则至少出现过三四次躁狂症状,还有一些研究规定了发病的最低年数。这些差异导致了单相躁狂症在双相障碍中的占比从1.1%跨越到65.3%。
迄今为止,大部分已完成的研究还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大部分研究中,研究人员简单地要求患者回顾以往的经历,这样不仅低估了抑郁的发作过程,也会夸大对单相躁狂症的预估。具有前瞻性的、更好的研究是随访患者数年,并进行周期性的评估。“我们真正想要的患者是在生活中经历过多次躁狂,但没有经历过抑郁”,杨说。“我遇到的第一个女士,她在21岁时第一次躁狂发作,在60多岁去世的时候,一直未经历过抑郁。这件事很有说服力。”
周期最长的一项躁狂症研究,是由美国布朗大学沃伦·阿尔特佩特医学院的心理学家戴维·所罗门(David Solomon)领导并于1978年开始的,研究结果于2003年发表。这项研究共涉及了229位双相障碍患者,其中27人是没有抑郁史的躁狂症患者。研究人员对这27位患者随访长达了20年,其中7位患者在整个期间内都没有出现过抑郁。研究结果显示,在229例患者中,单相躁狂症患者的占比为3%。
所罗门不主张为单相躁狂症创建单独的诊断措施,除非将来的研究能确定其在基因机制、干预或治疗上与双相障碍存在差异。如果研究中的发病率针对的是普通人,那么在美国,单相躁狂症患者的人数将约为10万人。而在整个世界范围里,更是有超过百万的患者。
不过,单相躁狂症患者的故事,也让一些精神病学家相信这种疾病需要被单独诊断。波特兰的滑雪教练林赛(Lindsey),就是这样的一个患者。18岁时,她出现了第一次的躁狂经历。到36岁时,她一直未经历过抑郁,但她还是被诊断为双相障碍。“我知道我是最快乐的那个人”,她说,“我从来不接受诊断结果。”她拒绝接受治疗,随着疾病的发作,她5次住进医院,不止1次被抓进监狱。
林赛的躁狂发作以欣快感开始,但会螺旋式地进入幻觉和表达困难的阶段。躁狂的时候,她不会觉得疲劳、饥饿或疼痛。20多岁时,有一次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徒步旅行时,躁狂症突然发作。林赛幻想世界末日到了,并告诉了父亲。她的父亲立刻飞过去,试图把她接回了缅因州的家中。她的父亲说:“她有药物,但从不服用。”在纳什维尔停留了一晚后,第二天早晨,林赛假装在酒店弹琴,惹恼服务员叫来警察,她趁乱开着警车逃跑了。
在接下来的冒险中,她故意迷路,在铁路轨附近弃车并埋了行李。她跳上一辆货运火车,在田纳西州中部的农村地区下车。从一个岩壁的山谷中爬出来后,她走进一个小教堂。那里的牧师,获得了她父亲的联系方式。
后来,林赛趁父亲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休息时,又逃跑了。找到她时,她正在高速公路围栏外的通电区域采摘雏菊。警察来了之后,劝她和父亲一起离开,但她拒绝和父亲离开,坚持想要被逮捕。在牢房里,一名警卫用辣椒水喷了她,最后把她关进了监狱顾问的办公室。林赛几乎不能说话,但她在黑板上反复写着“单相”。监狱顾问在阅读了关于林赛的症状描述后认为,她们的这次相遇恰恰是一个让林赛接受药物治疗的契机。监狱顾问给她服用了奥氮平(一种安定药物)后,她就恢复了。直到今天,林赛还在服药,尽管她还是会抗拒。她说:“药物就像是一剂充满悲伤、饥饿、疲劳和疼痛的毒药。”林赛在整个病症发作的过程中都是兴奋的,即使被喷辣椒水时也是如此,但这会让周围的人感到痛苦。她说:“我觉得这个病让我很开心,但我这样是自私的,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家庭。”
2015年,林赛在最后一次住院后不久,嫁给了一位名叫安迪(Andy)的记者。安迪说:“这种疾病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牢固。我会经常去看她。她慢慢地恢复了理智,这让人印象深刻。”在治疗中,林赛最看重的是,外科医生是否承认她不是患有躁郁症。林赛说:“当这一点被忽视时,我就不再相信那个医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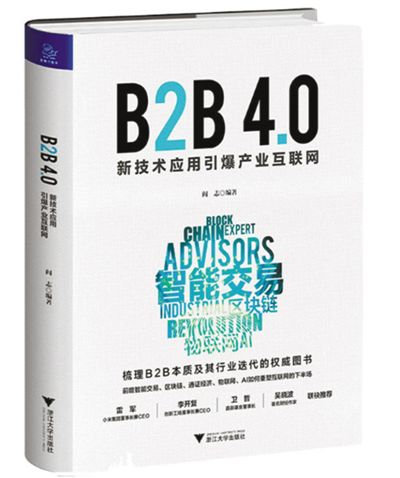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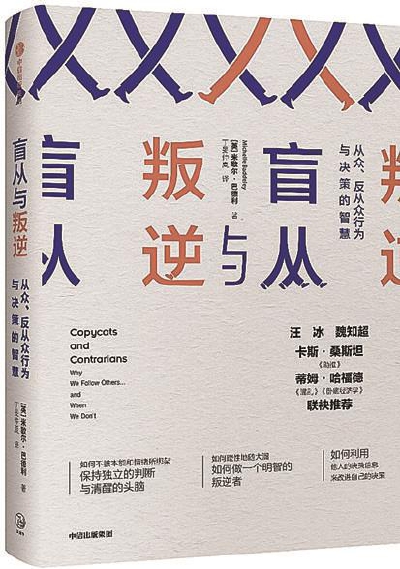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