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高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案件范围来看,家事纠纷是指发生于婚姻家庭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特定身份关系,这种特定身份关系源于婚姻的缔结、血缘的生理属性以及拟制血缘关系等,往往又以“婚姻家庭”这一特有的实体形式得以体现。从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角度来看,改革家事审判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家庭伦理,要理解和建构家事审判制度,必须以对婚姻家庭伦理的合理把握为基础,它构成了家事审判制度理论大厦的基石,并由此从根本上指导着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
家庭是一种伦理性共同体
婚姻家庭作为一类共同体,它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之中最基础性的存在,但它又不同于社会、国家、民族等共同体,而具有某种伦理特性。在一般的共同体中,其成员往往基于某种共同利益,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以达至某种目的。婚姻家庭具有上述共同体的一般特征,但其往往由于成员之间特定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家庭亲疏关系,其遵守的共同规则往往具有很强的伦理性,这种伦理性的特质往往源于爱,并基于爱而形成特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可以说,伦理性构成了婚姻家庭的内核,所有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关系都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为和社会关系,婚姻家庭成为“摆脱夫妻任性的伦理实体”。(杨怀英:《中国婚姻法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1页)婚姻家庭虽然作为人类社会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但又远不同于一般的财产和人身关系。正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伦理本质,马克思提出“离婚者的任性应该服从婚姻的任性”之著名论断。“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零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的境况和他们的财产状况也是不能由父母任意处理、不能让父母随心所欲来决定的。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就会像友谊一样,不是立法的对象了”。(庞正:“婚姻关系的法理解释——重读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有感”,《法律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婚姻家庭的社会伦理性及其承载的重要功能,决定了婚姻家庭关系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法律关系的解除,即便是夫妻双方的意志和行为也不能随心所欲。在婚姻共同体中,夫妻婚姻关系的解除已经不能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人之任性,需要顾及家庭,这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婚姻绝不仅仅只是两个人的幸福和美好,还关涉婚姻家庭整个共同体的幸福和善。
家庭这一伦理实体性存在虽然以“自然性”的存在为基础,肇始于自然性,但其最关键的往往超越了这种自然性的存在,成为一种基于血缘关系为前提的伦理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家庭关系……是以牺牲人格为其实体性的基础”。([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页)一方面,家庭由于这种自然天成的血缘关系而形成一种基于自然的等级秩序和相互依存关系;另一方面,这种自然的等级秩序和依存关系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之中的关系,相对于一般共同体之中个体的任性和自私自利,各个家庭成员往往受限于家庭这一整体。在这个“自然性”伦理实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作为其成员服务于这个自然伦理共同体。在这里所谓个人不能作为完全意义上的共同体,是相对于完全自利的个体而言的,每位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都需要同家庭伦理实体这一普遍性的存在服务,个人之于家庭就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家庭成员应当摒弃个人的私利,完全不同于个人的肆意妄为,在这里个人的自由受制于家庭这艘巨轮,和其他成员应当同舟共济、共担风雨,往往展现的是父母之恩、夫妻之爱、兄妹之情,这恰是家庭自然伦理实体精神的体现和本质体现。在婚姻家庭中,夫妻关系也罢,父母与子女关系也罢,都完全不同于契约关系中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双方,任何一方在人格、身份财产等关系上都是独立的,合同只约束双方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商定的事项,其核心是意思自治,双方可以基于意思自治而建立、变更、消灭这种合同法律关系。但在婚姻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不是契约性的,这种伦理性便不能完全体现意思自治,不能完全遵照个人的意思,父母不能因子女的过错,哪怕是再重大的过错,而放弃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这种不以家庭成员自由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背后恰恰是家庭特殊伦理性的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成员部分人格和自由,以这种牺牲或义务的强制履行来维持家庭的伦理性。
由爱而生的家庭伦理性规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明确表达了家庭关系是人类第一个社会关系的思想,家庭是“直接”“自然”的伦理实体,“以爱为其规定”。这意味着家庭是以血亲自然关系为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伦理实体,这种实体具有自然血亲的特性,更具有其关键性的社会属性——爱是家庭的伦理精神,这种爱是基于自然血亲的同一性的自然之爱,这种自然性所具有的爱往往是不需要理由的。
作为家庭伦理精神的爱,就是使“我”成为这个自然伦理实体中的一员,并为这个伦理实体所设定。“我”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然而这个自然的存在并不是指向生命肉体本身这种自然性,而是指一种自然的伦理关系、自然的伦理实体性存在:由于“我”生命肉体形成所构成的自然的伦理关系及其自然血亲性关系的伦理实体性存在。正是在这个血亲性自然伦理实体中,“我”摆脱了自身的抽象性,得到了规定,成为一个具有规定性的具体社会成员。(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8页)这种规定性的社会成员不同于契约形式下的个人,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伦理实体之中的一员,这种个人往往因为家庭的存在才有意义。在家庭之中,才存在着好夫妻、好父母、好子女,进而才会产生在家庭伦理实体中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基于这种特殊身份伦理关系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也恰恰是这种基于家庭伦理的爱才让这种关涉家庭的规定性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关系的特殊性,在这种关系中,让这个伦理实体的爱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不仅包括基于两性基础之上的情感和爱情,还将其中的友爱、慈爱、孝爱,构成从两性间、同伴间、代际间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定,真正的家庭伦理实体必然是上述几种关系的统一,我国古代称之为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兄友弟恭正是表达了家庭这一丰富的伦理内涵。
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性规定又完全不同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伦理性,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多地体现为意思自治,只要这种意思自治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社会利益即可。但对于家庭成员之间,除了遵守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要求和规定之外,还对家庭成员之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体的尊严和感受上,还要表现在对个人之上家庭整体性的尊重和保全,甚至需要为了家庭整体性利益而需要压抑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
正是基于爱,让这个家庭伦理实体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并呈现其规定性的异质性,尤其在对个人的重塑方面发挥着革命性的力量,恰恰是这种家庭伦理实体所体现出来的爱,让一个人必然经历从“孤独自我的否定”到“在他人身上肯定自我”再到“自我与他人的统一”。在“孤独的自我”状态下,一个人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甚至自私自利,因为全世界即是他,他即是全世界,本身无所谓对错。而当一个人进入家庭伦理实体这种群体状态之中,个人才会获得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一个孤独的自我和另一个孤独的自我相遇的时候,恰是一个人的自私自利、肆无忌惮与另一个孤独自我的碰撞,唯有对之前各自孤独自我的否定,才能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肯定。这种肯定往往是基于爱本身,为了爱抛弃孤独的自我,在他人身上获得重新的自我,为了爱可以让一个人放弃原始状态下的自我的一切不利于爱的因素,最终达至自我与他人的统一。为了爱让他们放弃了孤独的自我,为了爱让他们走在一起,每个人都因为爱和家庭而获得了重新的自我。
在这个婚姻家庭中,伦理性表现为它不同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义务,而呈现为更强的义务性和责任性。婚姻家庭中成员之间,不仅表现在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和伦理性,甚至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这种关系的要求。比如在特定情况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抚养义务,以及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赡养辅助义务,甚至是女婿或儿媳妇对岳父岳母或公婆的赡养义务,这种要求超越一般法律关系中的要求,更多地体现在婚姻家庭中,对成员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种要求恰恰是家庭伦理性特质的体现。司法很多时候就需要关照这种伦理特质的要求,比如在继承案件中,打破配偶、父母子女作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或指定监护人的过程中考虑这些特殊之处,而将其推向前台,其中往往伴随着特有的司法方式和司法程序,不能简单地适用法律,而忽略了其中的伦理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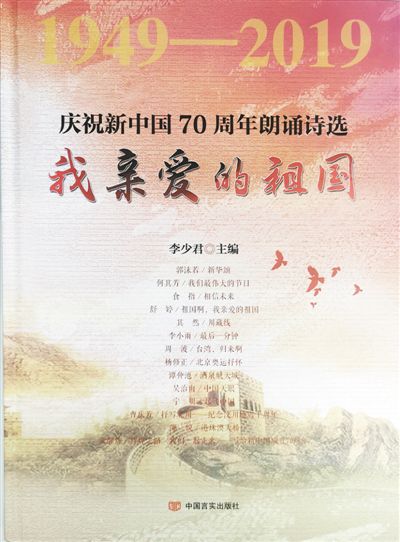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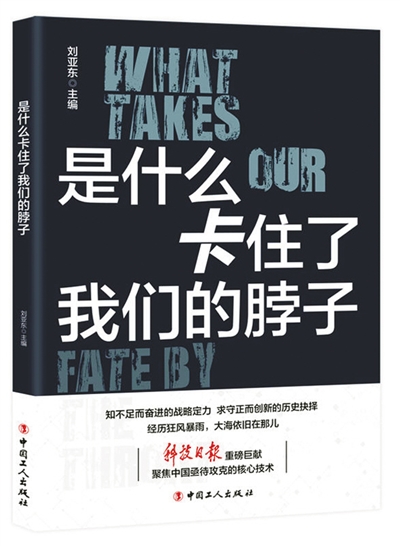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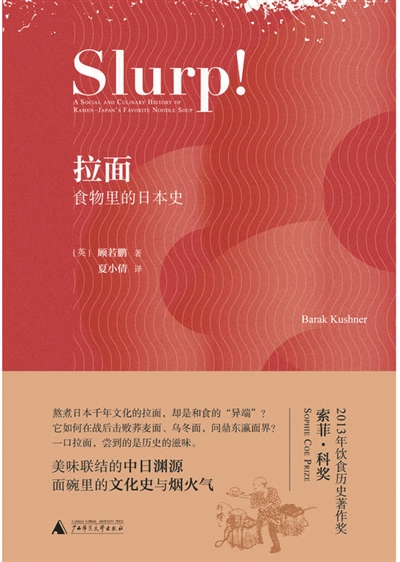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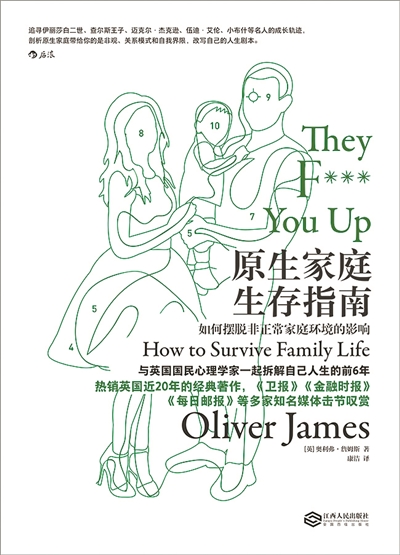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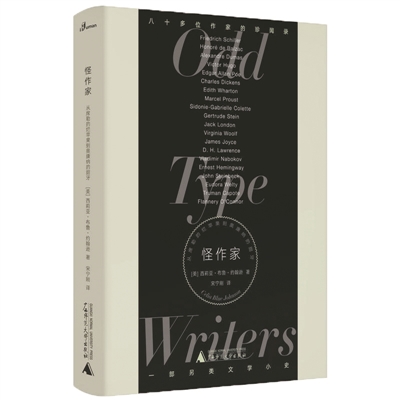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