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丹心谱》的成功,苏叔阳正式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在此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佳作问世,而且不局限在一个领域。
话剧方面,苏叔阳陆续发表了《金水桥畔》(1979)、《左邻右舍》(1980)、《家庭大事》(1982)、《灵魂的审判》(1984)、《太平湖》(1986)、《萨尔茨堡的雨伞》(1988)、《飞蛾》(1993)、《月光》(2000)等。《左邻右舍》被认为是苏叔阳的风格成熟之作,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剧本奖。
作为北影厂编剧,苏叔阳也写了不少电影电视剧本,比如《春雨潇潇》(1979)、《盛开的月季花》(1979)、《丹心谱》(1980)、《夕照街》(1983)、《一叶小舟》(1983)、《故土》(1984)、《我的爸爸我的妈妈》(1985)、《假脸》(1986)、《苏禄国王与中国皇帝》(1987)、《开采太阳》(1992)、《新龙门客栈》(1992)、《未完成的交响乐》(1995)、《周恩来——伟大的朋友》(1997)、《李知凡太太》(1999)、《国歌》(1999)等。《夕照街》则是他公认的代表作。
而在小说方面,苏叔阳1979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刚刚的眼睛》,其后的中短篇主要结集为《婚礼集》(1984)、《假面舞会》(1987)、《老舍之死》(1992)等小说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驾驭不同风格的功力。
限于篇幅,我们就简单谈谈其中两篇,一是1981年发表的《泰山进香记》,二是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生死之间》。
《泰山进香记》于1983年以其艺术上的创新,被李陀、冯骥才选入《当代短篇小说43篇》。从题材上说,这篇乡土味浓厚的小说可以归入广义的改革小说范畴,讲述了一位农村老妇无视作为支书的长孙的劝阻,克服高龄和险途,勇攀泰山向神明还愿的喜剧故事,语言诙谐幽默,略带温和的暗讽,却并不流于刻薄。
《泰山进香记》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物质增长和精神愉悦为背景,叙述农民将国家政策与神明护佑混为一谈的态度,但并未特别明确地作出褒贬,一方面似乎致敬了鲁迅早年文言论文中对底层民众“朴素白心”的辩护,一方面又内含了左翼文学的反封建主题,体现了一种对底层生活、世俗人心的包容情怀。
《生死之间》则涉及了城市中的一种特殊职业,讲述一名火葬场火化工人与一名妇产科助产士之间的爱情故事,一者送走死者,一者迎来生者,构思相当精巧,在题材上与香港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1983)遥相呼应。当然,这部小说具有改革上升期典型的正能量,与西西充满颓废气息的香港故事截然不同。
除短篇小说之外,苏叔阳还于1984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故土》,当年即获得首届人民文学奖。
在诗歌创作上,苏叔阳出版过诗集《关于爱》(1984)、《等待》(2000)、长诗《世纪之歌》(1997)等。另外,他还广泛涉猎歌词、曲艺、散文随笔、评论等多种文类,以及获得首届国家图书奖的传记文学《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1982)。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苏叔阳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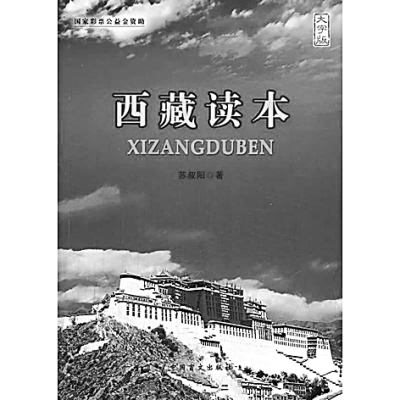
传承京味
在苏叔阳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众多作品之中,有两篇比较特别,一是小说《老舍之死》(1986),一是剧本《太平湖》(1986),都是他对前辈大师老舍先生的致敬之作。
《老舍之死》想象老舍自杀之前的所思所为,让死者的灵魂直接出场进行长篇独白,以写实手法处理超现象情节,用心营造“现场效果”和“真实感”。当时,致敬“文革”中罹难的前辈作家,并不限于苏叔阳,比如汪曾祺的《八月骄阳》同样致敬老舍,陈村的《死》写的是傅雷,叙述手法各不相同。
但像苏叔阳这样一再致敬的却似乎不多。在《太平湖》中,他一改话剧分幕的一般做法,借用宋词的结构分为上下两阕,上阕写投湖之前的老舍,下阕则写老舍死后与他笔下的人物探讨“文革”灾难。这个剧本苏叔阳写得极苦,四易其稿才基本满意。
这样频繁的致敬,自然体现出老舍先生在苏叔阳心中的地位。实际上,不仅是苏叔阳,老舍可以说潜在地影响了新时期整整一批的北京作家,比如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冯骥才、冯苓植等,以至于有论者称其时甚至形成了一股“老舍风”。
苏叔阳无疑是“把老舍的血液输入新时期文学的最力者之一”。他自述要“唱一曲京韵大鼓”,通俗质朴,简约凝练,风趣幽默,接近老舍的“俗白”“清浅”“结实有力”的语言风格。其中,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北京的方言口语,比如“少不?我可得有哇”“得了,您呐”“闹了归齐”“兴许是”“这么着”“没承想”“指不定”“别介”“淡不丝拉”“大模四样”等等词汇,生动热闹。
在《左邻右舍》《夕照街》等剧本中,苏叔阳借鉴了老舍《茶馆》的谋篇技巧,以一个固定空间为核心,贯串起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物。除了苏叔阳,同样还有一批剧作家致敬老舍,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自觉,从老舍的《龙须沟》《茶馆》,苏叔阳的《左邻右舍》《夕照街》,到李龙云的《小井胡同》(1981)、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1988),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其共同的特点,即是突出了空间性,并具有一种“民族志”的品质。
文学地理是创作与评论界的一个有趣话题,尤其是小说与戏剧,需要接地气,因此地方性因素——文化的地方性、语言的地方性——便成为作家们书写的重要资源,以文字为材料,营造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原乡、文学之城。我们不难细数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的乡土作家群,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都市为背景的新感觉派、流亡关内追忆沦陷故土的东北作家群,到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群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及至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均体现了地方性因素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而老舍的存在,可说是文学界一人一城的最佳范例。他语言上的造诣,叙述上的功夫,成为后生晚辈学习之楷模,同时自然也要引发影响的焦虑。
致敬即招魂。逝者已矣,而文字长存,流风余绪,脉脉不绝。苏叔阳为人谦逊低调,他致敬前辈,却无超越之野心,便无过多焦虑。只是兢兢业业,作为时间之流中的一木一石,为北京这座文学之城添砖加瓦,略尽绵薄。



 ×
×